殉道者(2)
“大抵是的。”殉道者每一次说道这种话,都会虔诚的跪倒在地。
这是一种痛苦,他自己在骗自己,他骗自己不知道所谓追求的只是痛苦。
“凡所追寻之物,即使虚幻,亦可摇曳如风。”
“大抵是的。”
“凡所笃定之物,即使缥缈,亦可腾空如云。”
“大抵是的。”
“凡所献身之物,即使污秽,亦可轰烈如雷。”
“大抵是的。”
在一个神能塑造一切的世界中,追求真实不再有其固有意义。
“吾即火焰,吾即世界!”
这是一种无聊,他依然在自己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不知道所追求的只是无聊。
“……”
雷云和风暴在一位农场主的农场上方低语,共同商议着鲜血和死亡的细节。
“绑架案,目标携带枪械,劫持人质,情绪过激,建议远程狙击。”
一道雷光在天空中划过,如同开了刃的砍刀一般,书写下一笔黄色的巨痕,容易想象吧,身体大抵于这黑夜一样,渴望被划破,渴望被惊醒。
接着那色苍雷的是里面孩子的惨叫,他的双亲的血在谷仓中已经与雨水混杂,一同成为了土地的养分。
他看到了太多的血,太多的血。
少年恐惧的在角落缩成一团,在冷风和恐惧之下颤抖着,哭泣着,眼前的人,手上明明有一把猎枪,但是依然用刀一点点的折磨死了自己的双亲。
他害怕,但更多的,是心中的愤怒和杀意。
“没有视野,队长,这个天气无法实行远程狙击。”
胡子拉碴的队长在指挥室里一遍踱步,一遍大口吸食着嘴边的卷烟。
“全员,计划改变,突击任务确定,准备行动!”
殉道者狂喜的跑到了这个偏僻的农场,一切都这么熟悉,这是自己的发源地,他记得的。
雨声掩盖了他的一切,包括自己存在于世的感觉,一切感官刺激在他心中都只是症候……
“全员,准备突击!”
领头的队长一脚踹开谷仓的旁门,另一半还有队员从正门突入,皮靴一次又一次陷入泥泞又拔出的哇哇声,充斥着每一个队员的心脏,和天空的惊雷,狂欢的劲风一同演奏着凶手的镇魂曲。
这是一种痛苦,他自己在骗自己,他骗自己不知道所谓追求的只是痛苦。
“凡所追寻之物,即使虚幻,亦可摇曳如风。”
“大抵是的。”
“凡所笃定之物,即使缥缈,亦可腾空如云。”
“大抵是的。”
“凡所献身之物,即使污秽,亦可轰烈如雷。”
“大抵是的。”
在一个神能塑造一切的世界中,追求真实不再有其固有意义。
“吾即火焰,吾即世界!”
这是一种无聊,他依然在自己欺骗自己,欺骗自己不知道所追求的只是无聊。
“……”
雷云和风暴在一位农场主的农场上方低语,共同商议着鲜血和死亡的细节。
“绑架案,目标携带枪械,劫持人质,情绪过激,建议远程狙击。”
一道雷光在天空中划过,如同开了刃的砍刀一般,书写下一笔黄色的巨痕,容易想象吧,身体大抵于这黑夜一样,渴望被划破,渴望被惊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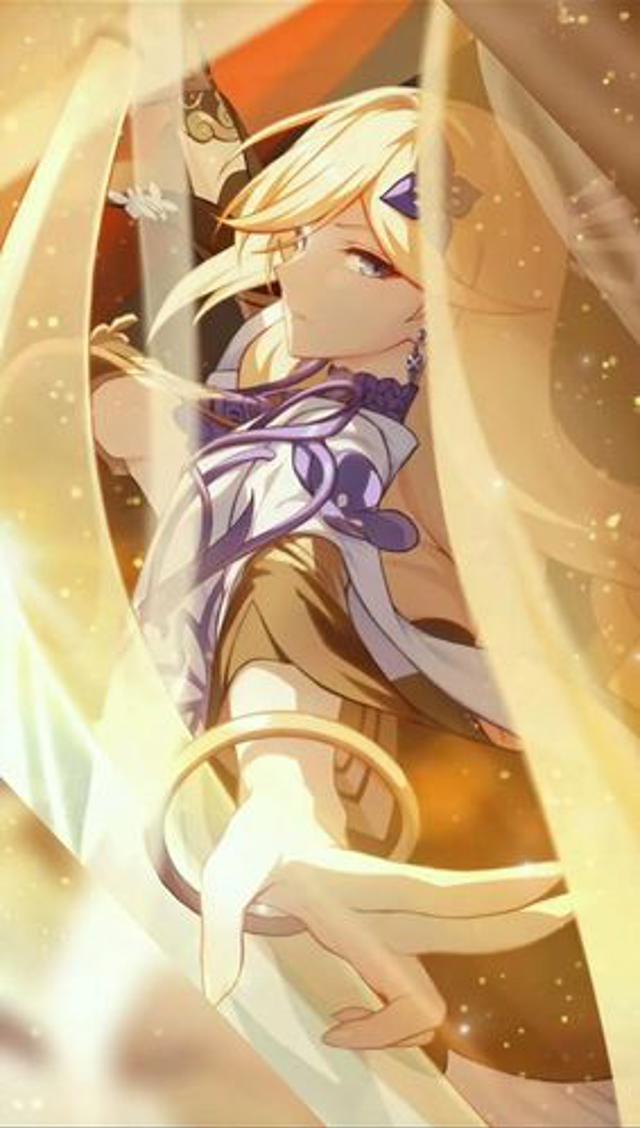
接着那色苍雷的是里面孩子的惨叫,他的双亲的血在谷仓中已经与雨水混杂,一同成为了土地的养分。
他看到了太多的血,太多的血。
少年恐惧的在角落缩成一团,在冷风和恐惧之下颤抖着,哭泣着,眼前的人,手上明明有一把猎枪,但是依然用刀一点点的折磨死了自己的双亲。
他害怕,但更多的,是心中的愤怒和杀意。
“没有视野,队长,这个天气无法实行远程狙击。”
胡子拉碴的队长在指挥室里一遍踱步,一遍大口吸食着嘴边的卷烟。
“全员,计划改变,突击任务确定,准备行动!”
殉道者狂喜的跑到了这个偏僻的农场,一切都这么熟悉,这是自己的发源地,他记得的。
雨声掩盖了他的一切,包括自己存在于世的感觉,一切感官刺激在他心中都只是症候……
“全员,准备突击!”
领头的队长一脚踹开谷仓的旁门,另一半还有队员从正门突入,皮靴一次又一次陷入泥泞又拔出的哇哇声,充斥着每一个队员的心脏,和天空的惊雷,狂欢的劲风一同演奏着凶手的镇魂曲。

 火影忍者木叶女忍者的耐力测试
火影忍者木叶女忍者的耐力测试












![【扫文】《[徐伦]北美殉道者花园》神仙一样的百合文学](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408/153138_84705.jpg)
![【扫文】《[徐伦]北美殉道者花园》神仙一样的百合文学](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220/153825_06930.jpg)
![【扫文】《[徐伦]北美殉道者花园》神仙一样的百合文学](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24/150742_15212.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