踽踽(贰)(2)
程蝶衣一惊,下意识想抽回手,却不知为何逐渐放松下来,由着他握着自己的手,程蝶衣在一瞬间有些失神,他已经想不起上一次有人这样拉着自己的手对自己说出这样关切地话语时,是什么时候了。
“没事的十二少,我……”他眼眶一酸,晶莹的泪就聚在眼底打转,不是为他寄人篱下成为玩物的境遇,而是为身边人关怀备至而并不是对他嗤之以鼻的感动,陈振邦的力道逐渐收紧:“蝶衣,他对你……”
随着他的手不停摇晃,程蝶衣再也禁不住落下泪来,其实他不愿哭的,这么些年了,什么没忍受过,这明明在他的世界里根本不足为奇。
陈振邦一愣,慌了神,扯起衣袖急急地给他擦泪,口中还念念有词:“蝶衣,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惹你这么伤心。”
“不,不是的,”程蝶衣努力平复情绪,轻轻笑道:“是除了十二少,已经没人再对我如此好了。”
陈振邦心里一阵酸。
那天他们聊了许多,聊彼此的人生,聊不同的境遇,程蝶衣羡慕陈振邦有美好的家庭,温馨的童年,他在谈起他小时候那些种种痛苦的经历时,总一笑而过,以饱经沧桑的心,容纳一切不公平。
陈振邦听着程蝶衣一字一顿地说着他这坎坷的二十年:原来他也是少年,却已那样风雨飘摇,让人心碎。
那天,陈振邦拉着程蝶衣瘦削的手,很富有志气地向他保证:
“蝶衣,我以后,再不会让你受欺负!”
程蝶衣浅浅一笑。
自己的命运本就薄如蝶衣,华美但易碎,这是他第一次,尝得一个人告诉他,他愿好好保护这件蝶衣,而不是将它穿在身上四处炫耀的滋味。
他心里温暖如春。
过了几月,他们的相处更加密切,陈振邦每日都会到戏园子捧场,蝶衣也一日比一日放的开,经常拉他去吃小吃,坐龙舟,他们在不自觉间已成了挚友,那是一种知己难逢的喜悦。
终于有一天,陈父发来了电报,要陈振邦回家,说是不能再让他浪荡过度,得回来收收心,准备着继承家业了。
陈振邦纵是万般的不情愿,无奈家父之言终究难违,那日下午去找蝶衣,给他说了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蝶衣甚是惊讶,但也怅然若失地点了头:“家业重要,你以后是要好好娶妻生子的,可不能误了事。”
说这话时程蝶衣的手在抖,害怕他看见,忙装着若无其事取银钗,今天他要演贵妃,可真是应了景,贵妃离了玄宗,他也要与他就此别过了。
两人都是满腹心事,却谁也没对谁说,只堪堪作了告别,陈振邦说今天听完最后一场戏就要回去,到时候会有人接他。他胆战心惊踌躇不已的说完了这番话,见蝶衣并没有回头,只好深深吸了一口气:“蝶衣,你放心,我以后成了器,一定不让你受欺负,你等我几年,我还到这里找你。”
“没事的十二少,我……”他眼眶一酸,晶莹的泪就聚在眼底打转,不是为他寄人篱下成为玩物的境遇,而是为身边人关怀备至而并不是对他嗤之以鼻的感动,陈振邦的力道逐渐收紧:“蝶衣,他对你……”
随着他的手不停摇晃,程蝶衣再也禁不住落下泪来,其实他不愿哭的,这么些年了,什么没忍受过,这明明在他的世界里根本不足为奇。
陈振邦一愣,慌了神,扯起衣袖急急地给他擦泪,口中还念念有词:“蝶衣,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惹你这么伤心。”
“不,不是的,”程蝶衣努力平复情绪,轻轻笑道:“是除了十二少,已经没人再对我如此好了。”
陈振邦心里一阵酸。
那天他们聊了许多,聊彼此的人生,聊不同的境遇,程蝶衣羡慕陈振邦有美好的家庭,温馨的童年,他在谈起他小时候那些种种痛苦的经历时,总一笑而过,以饱经沧桑的心,容纳一切不公平。
陈振邦听着程蝶衣一字一顿地说着他这坎坷的二十年:原来他也是少年,却已那样风雨飘摇,让人心碎。

那天,陈振邦拉着程蝶衣瘦削的手,很富有志气地向他保证:
“蝶衣,我以后,再不会让你受欺负!”
程蝶衣浅浅一笑。
自己的命运本就薄如蝶衣,华美但易碎,这是他第一次,尝得一个人告诉他,他愿好好保护这件蝶衣,而不是将它穿在身上四处炫耀的滋味。
他心里温暖如春。
过了几月,他们的相处更加密切,陈振邦每日都会到戏园子捧场,蝶衣也一日比一日放的开,经常拉他去吃小吃,坐龙舟,他们在不自觉间已成了挚友,那是一种知己难逢的喜悦。
终于有一天,陈父发来了电报,要陈振邦回家,说是不能再让他浪荡过度,得回来收收心,准备着继承家业了。
陈振邦纵是万般的不情愿,无奈家父之言终究难违,那日下午去找蝶衣,给他说了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蝶衣甚是惊讶,但也怅然若失地点了头:“家业重要,你以后是要好好娶妻生子的,可不能误了事。”
说这话时程蝶衣的手在抖,害怕他看见,忙装着若无其事取银钗,今天他要演贵妃,可真是应了景,贵妃离了玄宗,他也要与他就此别过了。
两人都是满腹心事,却谁也没对谁说,只堪堪作了告别,陈振邦说今天听完最后一场戏就要回去,到时候会有人接他。他胆战心惊踌躇不已的说完了这番话,见蝶衣并没有回头,只好深深吸了一口气:“蝶衣,你放心,我以后成了器,一定不让你受欺负,你等我几年,我还到这里找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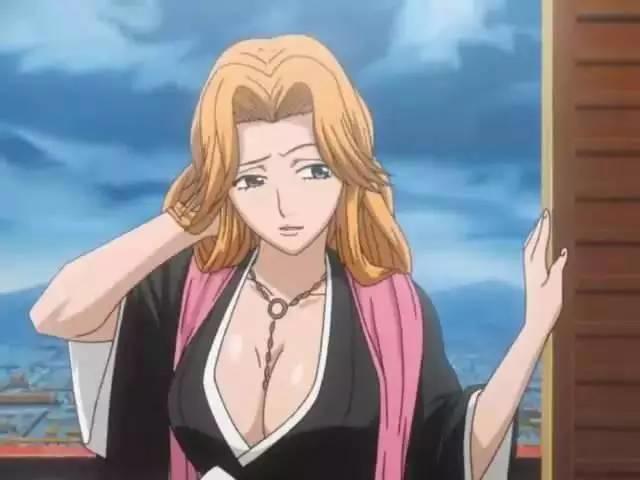
 ao3fog
ao3f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