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意义(2)
但他一天也未曾放弃过这个梦。
于是他回国之后疯狂地寻找,像中国早些年最俗情的消费文学一样,他“踏遍他们在十一月夜里一起踏过的街道,再次造访他们开着她的白色小轿车去过的偏僻地方”,“这里到处弥漫着忧郁的美,即使黛西已经不在了”。
仿佛是他把她弄丢了。
他绝望地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充斥着忧郁、又因她而美的城市,“一切都在他朦胧的泪眼里消逝的太快,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最新鲜最美好的已经永远失去了。”
最残忍的是,彼时的黛西已经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叫汤姆·布坎南的男人,他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强悍的美式足球边锋,美国富人阶层的完美代表。
但我并不想提及这两个人更详尽一点的事。正如书中所说:“上帝注视着一切。”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后来他们定居在纽约东边的长岛东卵,房子码头有一盏绿灯,会在夜晚发出和星辰相比微弱似无的光。
它是盖茨比穷尽一生的希望。但它最终黯淡了下去,消匿于天际。
盖茨比的别墅位于西卵,和那盏幽暗的绿灯隔了一整个海湾。每到星期五,音乐、香槟和灯火会在盖茨比的巨大的房子里彻夜供应,往返的人群从早上九点到午夜过后络绎不绝,人人都知道“盖茨比”和盖茨比的派对,但没人真正晓得谁是盖茨比,事实上也没人在乎这位没有任何背景、从前也不被人所熟知的、突然跻身于美国上流社会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人们只在乎他是以何种罪恶的方式爬上高级阶层,因此甚至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
“会做这种事的人就是有些奇怪,”“人家觉得他曾经杀过人”,“应该是说他在大战时期曾经当过德国间谍”。
盖茨比听得到这些,他无所谓别人说过什么,却又无比惧怕无人相信他。不如说他最怕这些传到黛西的耳朵里。
他是狂欢派对的发起者,亦是上帝的孤独者。他滴酒不沾,站在上帝的视角默默地在来宾中搜寻着什么,又或者只专注于头顶哪一片星空属于他,以及那盏微弱的绿灯,他何时才能真正拥抱它。
如此频繁的派对,周复一周,整个纽约都家喻户晓,但他只希望有朝一日,她也可以慕名而来。
他想了一千种见她的方式。
盖茨比和黛西久别重逢的那一天,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像个傻子一样把尼克的屋子装满了鲜花,又满意地以黛西的视角看着自己的建筑物。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看到或等待期待已久的人光临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屋子,就会慌慌张张地以他的角度看一遍自己发过和摆放的那些东西,然后一边怀着忐忑的心一边自以为是地认为很完美。
那天下午盖茨比让自己在雨里泡了一个下午,然后慌张又悲惨地站在门口。直到见到久别重逢的黛西,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安放。
在此之前,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盖茨比这样做,然后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故友。
攀谈过后,我突然真正明白了那是什么,那种力量从心底油然而生,然后挤挤攘攘地侵入四肢百骸,抵达我每一个指尖和发端,它们推搡着我,我身体里暗涌流动——我想要开口说点什么,但眼神交叉的那个短暂的瞬间,我多希望他能够明白一些我无法言说的东西。
于是他回国之后疯狂地寻找,像中国早些年最俗情的消费文学一样,他“踏遍他们在十一月夜里一起踏过的街道,再次造访他们开着她的白色小轿车去过的偏僻地方”,“这里到处弥漫着忧郁的美,即使黛西已经不在了”。
仿佛是他把她弄丢了。
他绝望地离开这个城市——这个充斥着忧郁、又因她而美的城市,“一切都在他朦胧的泪眼里消逝的太快,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最新鲜最美好的已经永远失去了。”
最残忍的是,彼时的黛西已经结了婚,嫁给了一个叫汤姆·布坎南的男人,他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强悍的美式足球边锋,美国富人阶层的完美代表。
但我并不想提及这两个人更详尽一点的事。正如书中所说:“上帝注视着一切。”但有一点必须要说,后来他们定居在纽约东边的长岛东卵,房子码头有一盏绿灯,会在夜晚发出和星辰相比微弱似无的光。
它是盖茨比穷尽一生的希望。但它最终黯淡了下去,消匿于天际。
盖茨比的别墅位于西卵,和那盏幽暗的绿灯隔了一整个海湾。每到星期五,音乐、香槟和灯火会在盖茨比的巨大的房子里彻夜供应,往返的人群从早上九点到午夜过后络绎不绝,人人都知道“盖茨比”和盖茨比的派对,但没人真正晓得谁是盖茨比,事实上也没人在乎这位没有任何背景、从前也不被人所熟知的、突然跻身于美国上流社会房子的主人究竟是谁,人们只在乎他是以何种罪恶的方式爬上高级阶层,因此甚至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
“会做这种事的人就是有些奇怪,”“人家觉得他曾经杀过人”,“应该是说他在大战时期曾经当过德国间谍”。
盖茨比听得到这些,他无所谓别人说过什么,却又无比惧怕无人相信他。不如说他最怕这些传到黛西的耳朵里。
他是狂欢派对的发起者,亦是上帝的孤独者。他滴酒不沾,站在上帝的视角默默地在来宾中搜寻着什么,又或者只专注于头顶哪一片星空属于他,以及那盏微弱的绿灯,他何时才能真正拥抱它。
如此频繁的派对,周复一周,整个纽约都家喻户晓,但他只希望有朝一日,她也可以慕名而来。
他想了一千种见她的方式。
盖茨比和黛西久别重逢的那一天,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像个傻子一样把尼克的屋子装满了鲜花,又满意地以黛西的视角看着自己的建筑物。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看到或等待期待已久的人光临自己的社交圈或是屋子,就会慌慌张张地以他的角度看一遍自己发过和摆放的那些东西,然后一边怀着忐忑的心一边自以为是地认为很完美。
那天下午盖茨比让自己在雨里泡了一个下午,然后慌张又悲惨地站在门口。直到见到久别重逢的黛西,他一直不知道自己该往何处安放。
在此之前,我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盖茨比这样做,然后我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故友。
攀谈过后,我突然真正明白了那是什么,那种力量从心底油然而生,然后挤挤攘攘地侵入四肢百骸,抵达我每一个指尖和发端,它们推搡着我,我身体里暗涌流动——我想要开口说点什么,但眼神交叉的那个短暂的瞬间,我多希望他能够明白一些我无法言说的东西。
 缩小生存游戏2
缩小生存游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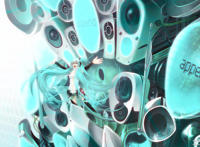


















![[碧蓝航线同人 番外篇]存在的意义](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45543_00171.jpg)
![[碧蓝航线同人 番外篇]存在的意义](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613/170437_97158.jpg)
![[碧蓝航线同人 番外篇]存在的意义](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13/151327_09151.jpg)
![[碧蓝航线同人 番外篇]存在的意义](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29/162110_0350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