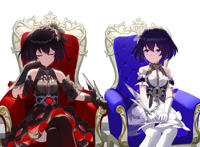三体:程心(2)
他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动作并不优雅,颇有几分道不同不与为谋的意思。我瞧出来了,只得随他意思离开。
经过他身侧的时候,刚好摸到衣兜里有两颗水果糖,下意识掏出来塞进他口袋,似一种隐秘的心照不宣。这个动作使我自己都惊讶。
但随即我想,我潜意识想要告诉他的是,人类世界再怎么有悲观之处,只要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会有人性善良存在。多品一品甜,也许就不会执着于借助外界利刃锋芒,一股脑斩杀所有光明与黑暗。
叁——
分崩离析。
三个世纪后的风拂过鬓发一角,它的力道十分轻柔,正如这个年代所有人的特点——纤细柔弱如飘摇的芦苇,或许只需微微一触便会破碎成星辰粉末在空中。曾经在我眼中属于永恒的星星们正按部就班地向地球散发光芒,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碳氢元素组成了它的身躯。如今我得知星星也会死去,蒸汽自心脏而出冲破皮肤,将它再一次变为宇宙中点点的微光。
我在街头踟蹰半晌,终于毅然向广告牌走去。此前有六位公元的同类造访过我,托马斯·维德的子弹划破血肉的感觉仍使人不寒而栗。那些冷酷而残暴的人,新世界不能落入到他们的手中。对权力的追逐和渴望无疑会毁灭这个刚刚稳定的世界,虽说它不过是在罗辑凌厉目光下短暂存在的肥皂泡,一粒灰尘或是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让它破碎。此时此刻一位母亲送来她的婴儿,我将这个小生命拥进怀中,我也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来的,我也曾孤零零地躺在公园的长凳上,独自一人走向地狱,走向死亡。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如果没有母亲予我的爱,我只是文明坟墓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沙砾。
自三十八万年前细胞诞生以来,是爱使生命生生不息。蛮野的自然选择法则使生物向更残暴,更庞大的方向进化,而一只小鸟或是一只猫的生存靠的却是父母给予的爱。爱在风里,在溪流里,在清晨盛开花朵的瓣上,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中,在每一颗星星闪烁的光芒里。从远古到未来,只有爱能救赎地球,我想。
于是我只得向前一步,坚定地吐出几个字。“我将竞选执剑人。”我会成为那个最高音吗?
肆——
何日再远游
弗雷斯说,这不怪我。
巨大的灾难压迫得人无法思考,即使从理智上我也不愿承认错不在我,从情感上更甚。毕竟没有谁经历过那一刻,面前是智子即将入侵地球的警报,手里是决定两个命运生死的威慑控制器。我记不清我在那最后十分钟里想了什么,只记得在最后一秒,我像甩开一个怪物一样把威慑控制器丢得远远的。我惧怕它。我只想守护和平,从未预料到自己将面对战争。这是本能,但我想我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自责与愧疚。
难道就应该由一个独裁者,永远紧紧盯住敌人的眼睛?还是这一切都是地球注定承受的命运?那它为何又偏偏落到我身上?我盯着他,却又好像没在看着他,颇有些心不在焉。弗雷斯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他温和地说,孩子,事已至此,别想那么多,去睡一觉吧,明天早上太阳还会升起的。
经过他身侧的时候,刚好摸到衣兜里有两颗水果糖,下意识掏出来塞进他口袋,似一种隐秘的心照不宣。这个动作使我自己都惊讶。
但随即我想,我潜意识想要告诉他的是,人类世界再怎么有悲观之处,只要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会有人性善良存在。多品一品甜,也许就不会执着于借助外界利刃锋芒,一股脑斩杀所有光明与黑暗。
叁——
分崩离析。
三个世纪后的风拂过鬓发一角,它的力道十分轻柔,正如这个年代所有人的特点——纤细柔弱如飘摇的芦苇,或许只需微微一触便会破碎成星辰粉末在空中。曾经在我眼中属于永恒的星星们正按部就班地向地球散发光芒,不知从何处而来的碳氢元素组成了它的身躯。如今我得知星星也会死去,蒸汽自心脏而出冲破皮肤,将它再一次变为宇宙中点点的微光。
我在街头踟蹰半晌,终于毅然向广告牌走去。此前有六位公元的同类造访过我,托马斯·维德的子弹划破血肉的感觉仍使人不寒而栗。那些冷酷而残暴的人,新世界不能落入到他们的手中。对权力的追逐和渴望无疑会毁灭这个刚刚稳定的世界,虽说它不过是在罗辑凌厉目光下短暂存在的肥皂泡,一粒灰尘或是一个眼神都有可能让它破碎。此时此刻一位母亲送来她的婴儿,我将这个小生命拥进怀中,我也是从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来的,我也曾孤零零地躺在公园的长凳上,独自一人走向地狱,走向死亡。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如果没有母亲予我的爱,我只是文明坟墓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沙砾。
自三十八万年前细胞诞生以来,是爱使生命生生不息。蛮野的自然选择法则使生物向更残暴,更庞大的方向进化,而一只小鸟或是一只猫的生存靠的却是父母给予的爱。爱在风里,在溪流里,在清晨盛开花朵的瓣上,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之中,在每一颗星星闪烁的光芒里。从远古到未来,只有爱能救赎地球,我想。
于是我只得向前一步,坚定地吐出几个字。“我将竞选执剑人。”我会成为那个最高音吗?
肆——
何日再远游
弗雷斯说,这不怪我。
巨大的灾难压迫得人无法思考,即使从理智上我也不愿承认错不在我,从情感上更甚。毕竟没有谁经历过那一刻,面前是智子即将入侵地球的警报,手里是决定两个命运生死的威慑控制器。我记不清我在那最后十分钟里想了什么,只记得在最后一秒,我像甩开一个怪物一样把威慑控制器丢得远远的。我惧怕它。我只想守护和平,从未预料到自己将面对战争。这是本能,但我想我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自责与愧疚。
难道就应该由一个独裁者,永远紧紧盯住敌人的眼睛?还是这一切都是地球注定承受的命运?那它为何又偏偏落到我身上?我盯着他,却又好像没在看着他,颇有些心不在焉。弗雷斯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他温和地说,孩子,事已至此,别想那么多,去睡一觉吧,明天早上太阳还会升起的。
 第五人格心患车文过程超长
第五人格心患车文过程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