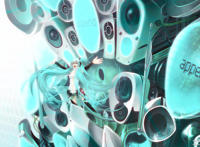一个女人的死(一)
沅阳镇一直以清凉而让人称道的石头建筑也没能有效抵御这股热浪的袭击,就像它无法抵御荷枪实弹的敖坡上的土匪。空气潮湿,仿佛能养鱼,而这些水气作为良好的导体,又将高温传遍小镇,无处不在,就连老鼠也躲在房梁上喘气不止。地上的人和狗就更糟糕了。野狗趴在本应该凉爽的青石板上——这是数十代野狗传下的经验——吐着舌头,耷着脑袋,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有着稀疏几根粗毛,还长满烂疮,向外面流着脓血。正午十分,阳光直射狭窄的街道,野狗随着影子的迁移也移到屋檐的一丁点阴处下,可还没能闭上眼休息一会,就会有人提着镰刀,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屋里赶来,这群狗又扯起干瘦的四腿快速散开。
穿衣是一种煎熬。那年代的布料吸水性着实不错,像海绵把身上的汗水和空中的湿气吸收饱和,然后贴在人身上,像是多张了一块皮,让人着实不适。正因为如此,男人总是光着膀子,甚至全部脱光,裸着身子在街上转悠,搂着喜欢的妓女直接进房里。妓女则整天躲在青楼上光着身子,等着接待生意。只是可怜了良家女子,要为了在外嫖娼的夫婿而穿戴整齐,一边还得管理家务。
镇长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女子,而且,做得更为优秀,在良家女子群体里出类拔萃。无论任何人任何时候在镇长家做客,都会感叹镇长夫人衣着的得体。在知了都偃旗息鼓的三伏天,她总是穿着白色碎花的旗袍,露出一双洁白的臂膊;而在冰锥结了一米多长的冬月,镇长夫人也只是穿着轻棉衣,坐在煤火旁,凹凸有致的身材得以彰显。与本地一百三十七个妓女不同,镇长夫人的眉宇、嘴唇虽然总是散发着让男人疯狂的诱惑,但她的五官组合在一块却总是一副让人望而生畏的表情。这种气质来源于她早年的生活经历,她出生于上海,今年三十五岁,与民国同年。她的父母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也接受过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最先进的教育。她懂得美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对于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也略知一二,因此,她也预言了她死后不久便爆发的内战,她懂得英语,在英国有过留学生涯,法语也说得不错。
本来,她和她的丈夫作为国民党的高知分子,是可以留在上海发展的,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不得不内迁,最后在蒋经国的建议下,他们接管此处,当了领导者。毕竟,这里是通往中国西南部的咽喉,张学良就关押在沅阳的上游。
她依然记得她和丈夫来到沅阳的那个有些遥远的冬日午后。那一天,政府宣布放弃南京,退守重庆。他们在官道上下了卡车,满目是高耸不齐的铁青着脸的山。两个马夫驾着一匹老马,拖着一辆破旧的马车,在此处恭候多时。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将为数不多的行李搬上车,然后回过身来请自己躺在行李上。马车夫一挥鞭,她开始感到身下传来一阵阵颠簸,天上的阴云也开始向后退去。
 前一个后一个会撑坏的雷帕
前一个后一个会撑坏的雷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