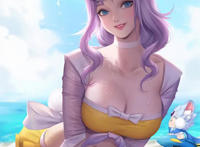唯梦闲人不梦君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白居易
故事依稀要从贞元十八年那一天说起。
二十五岁的元稹和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在长安准备冬季的吏部考试。
长安城中木叶稀疏,风声潇潇,秋景萧瑟难免勾起人们的悲秋之感。白居易回想起韶光已逝,而却已经有些年老体衰的苗头,且功业无成时,叹道:“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言语间满是萧瑟愁苦的滋味,就和长安城的秋一样,红叶满地,凉意也如此彻骨。
过往的大好光阴犹如离弦的箭,发间有着些许银丝的人倚着窗和枯木对望。
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诗,叹了口气,提笔写下几句宽慰白居易:“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星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差人送了过去。
白居易看到了诗,青年隽秀的字在纸张上流动,仿佛这首诗是温暖的阳光,带来了些许的慰藉。他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清凌凌的色彩,透着金色的光,洒在了红叶之上,温柔地笑了。白居易想起和元稹初见时的那双少年意气的眼,充满着对长安城的憧憬和向往,但又怀着豁达的笑意,让他想起了以前的自己,是生机勃勃而又美好的。长安的玉笛声飞扬,伴着满城的飘絮不知飞往了何家。青年爽朗的笑声和胡姬腰间的银铃声跳跃在酒肆中,少年人的模样,不过如此,但是又格外值得怀念。
是少年眼中的长安城,也是白居易眼中的长安城,承载着无数的文人墨客的凌云壮志的抱负和绮丽的梦,融化在长安城的这阵秋中,冰凉中又有着跳跃的希望,明亮而又炽热。
吏部考试顺利通过了,白居易和元稹同时舒了口气,又笑出了声。
“不如欢饮达旦,庆祝一番?”白居易笑道。
“好,那就这么定了。”元稹赞同。
地点定在了长安最负盛名的酒肆里,青石板路上积满了一层薄雪,青色的酒旗和悬挂在屋檐的灯笼随风摇动,灯光在夜色沉沉中闪烁着。寒风凛冽,行人稀少,而酒肆内弥漫着一股暖意和奇异的芬芳。元稹轻轻一嗅,倒是乐了。酒是好酒,客皆雅客,舞姬也具是美人。虽说天公不作美,但是好酒与玉人相伴,还是让人颇感心胸暖融融的。
元稹微醺,醉眼迷离地望着中央翩然起舞的舞姬,手执玉箸呵呵笑着,敲着薄胎的杯盏附和着乐人的丝竹鼓吹之声,呼吸间是浅淡的酒气。舞姬突然一个转身望向元稹,那张芙蓉面上沾着些红晕,一双眼黑白分明,水波盈盈,欲语还休。而元稹看见舞姬这样慌忙放下玉箸,连连摆手说道家中已有娇妻之类的话,白居易好笑地望着这一幕。
风打灯笼远,重楼酒旗飘。
梦中鸦鬓色,楚腰掌中舞。
但愿酒中眠,荒唐此片刻。
成为校书郎的日子轻松但是过得飞快,白居易后来回想起那时和同僚游闲月阁,和秘书省的官员在昆明池宴饮,琼觞醉月,坐花流云,就如曲水流觞一般,比拼诗文,消磨时光。但终不如和元稹在酒肆里喝酒那样令人畅快。所有人都卸下了面具,真实的一面却又格外的蛊惑人心。笑着,闹着,跳着,唱着,都是自我。
——白居易
故事依稀要从贞元十八年那一天说起。
二十五岁的元稹和三十二岁的白居易在长安准备冬季的吏部考试。
长安城中木叶稀疏,风声潇潇,秋景萧瑟难免勾起人们的悲秋之感。白居易回想起韶光已逝,而却已经有些年老体衰的苗头,且功业无成时,叹道:“不堪红叶青苔地,又是凉风暮雨天。莫怪独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言语间满是萧瑟愁苦的滋味,就和长安城的秋一样,红叶满地,凉意也如此彻骨。
过往的大好光阴犹如离弦的箭,发间有着些许银丝的人倚着窗和枯木对望。
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诗,叹了口气,提笔写下几句宽慰白居易:“劝君休作悲秋赋,白发如星也任垂。毕竟百年同是梦,长年何异少何为。”差人送了过去。
白居易看到了诗,青年隽秀的字在纸张上流动,仿佛这首诗是温暖的阳光,带来了些许的慰藉。他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的天空,清凌凌的色彩,透着金色的光,洒在了红叶之上,温柔地笑了。白居易想起和元稹初见时的那双少年意气的眼,充满着对长安城的憧憬和向往,但又怀着豁达的笑意,让他想起了以前的自己,是生机勃勃而又美好的。长安的玉笛声飞扬,伴着满城的飘絮不知飞往了何家。青年爽朗的笑声和胡姬腰间的银铃声跳跃在酒肆中,少年人的模样,不过如此,但是又格外值得怀念。
是少年眼中的长安城,也是白居易眼中的长安城,承载着无数的文人墨客的凌云壮志的抱负和绮丽的梦,融化在长安城的这阵秋中,冰凉中又有着跳跃的希望,明亮而又炽热。
吏部考试顺利通过了,白居易和元稹同时舒了口气,又笑出了声。
“不如欢饮达旦,庆祝一番?”白居易笑道。
“好,那就这么定了。”元稹赞同。
地点定在了长安最负盛名的酒肆里,青石板路上积满了一层薄雪,青色的酒旗和悬挂在屋檐的灯笼随风摇动,灯光在夜色沉沉中闪烁着。寒风凛冽,行人稀少,而酒肆内弥漫着一股暖意和奇异的芬芳。元稹轻轻一嗅,倒是乐了。酒是好酒,客皆雅客,舞姬也具是美人。虽说天公不作美,但是好酒与玉人相伴,还是让人颇感心胸暖融融的。
元稹微醺,醉眼迷离地望着中央翩然起舞的舞姬,手执玉箸呵呵笑着,敲着薄胎的杯盏附和着乐人的丝竹鼓吹之声,呼吸间是浅淡的酒气。舞姬突然一个转身望向元稹,那张芙蓉面上沾着些红晕,一双眼黑白分明,水波盈盈,欲语还休。而元稹看见舞姬这样慌忙放下玉箸,连连摆手说道家中已有娇妻之类的话,白居易好笑地望着这一幕。
风打灯笼远,重楼酒旗飘。
梦中鸦鬓色,楚腰掌中舞。
但愿酒中眠,荒唐此片刻。
成为校书郎的日子轻松但是过得飞快,白居易后来回想起那时和同僚游闲月阁,和秘书省的官员在昆明池宴饮,琼觞醉月,坐花流云,就如曲水流觞一般,比拼诗文,消磨时光。但终不如和元稹在酒肆里喝酒那样令人畅快。所有人都卸下了面具,真实的一面却又格外的蛊惑人心。笑着,闹着,跳着,唱着,都是自我。
 天梦和霍雨浩CP
天梦和霍雨浩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