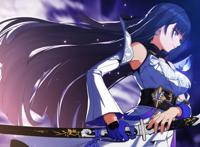无期迷途同人 海拉专场 治安官与唢呐(2)
既然已经打定主意去局里,海拉立刻准备实现自己的计划。在前贫民窟中央广场上有一家瑜伽店,陈设别致,大堆药瓶整齐摆放很是惹眼。海拉捡起块砖头往上砸去。锈火的成员从拐角跑来。海拉站定了不动,两手插在口袋里,对着斗篷直笑。“搞事的外来人在哪儿?”她们气急败坏地问。“你难道看不出我也许跟这事有点牵连吗?”海拉说,口气虽然带点嘲讽,却很友善,仿佛好运在等着她。在锈火的脑子里海拉连个当局狗腿都算不上。外来的人没有谁会留在这里等锈火。她们总是一股脑似的溜走。
广场对面有家热闹的肉铺,海拉在铺子旁坐下来,消受了一串豆干、一份鸡蛋仔、一份茶,以及一份炸面包片。吃完后她向老板坦白:她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也与她素昧平生。“手脚麻利些,去请个管事的来,”海拉说,“别让大爷久等。”“用不着惊动锈火的精英,”老板干净利落地把海拉往外一叉,正好让她左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
她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然后又掸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仿佛只是一个绯色的梦,那个局子远在天边。
一个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站在橱窗前,而离店两码远,就有一位彪形大汉——蛇眼的佣兵。海拉厚着面皮把小耗子该干的那一套恶心勾当一段段表演下去。佣兵在盯着。那被她偷窃的女子只消将手指一招,海拉就等于进安乐岛了。她想象中已经感到了巡捕房的舒适和温暖。年轻的女士却如藤蔓一样缠住了海拉。一拐弯,她甩掉女伴撒腿就走。海拉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紧闭着镇住了她,使她永远也不会被捕呢?
她顺着楼体贫民窟向下走去,因为即使她的家仅仅是辛迪加的破败一角,她仍然有夜深知归的本能。可是,在一个异常幽静的地段,海拉停住了脚步。这里有一座古老的殡仪馆,建筑古雅,不很规整,是有白墙的那种房子。
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花玻璃窗子映射出来,嘟嘟为了星期天的白事在苦练,刺耳的乐音飘进海拉的耳朵,把她胶着在螺旋形的铁栏杆上。昏暗的灯泡悬在中天,光辉、静穆,车辆与行人都很稀少,檐下的冻雀睡梦中啁啾了几声——这境界一时之间使人想起新城FAC总局边上的墓地。唢呐奏出的哀乐使铁栏杆前的海拉入定了,因为当她在生活中有局长、九十九、夜莺、军团以及安静舒适的居所与够用的钱财时,唢呐对她来说是很熟悉的。海拉这时敏感的心情和殡仪馆的潜移默化会合在一起,使她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她猛然对她所落入的泥坑感到憎厌。那堕落的时光,低俗的欲望,心灰意懒,才能衰退,动机不良——这一切现在都构成了她的生活内容。
广场对面有家热闹的肉铺,海拉在铺子旁坐下来,消受了一串豆干、一份鸡蛋仔、一份茶,以及一份炸面包片。吃完后她向老板坦白:她无缘结识钱大爷,钱大爷也与她素昧平生。“手脚麻利些,去请个管事的来,”海拉说,“别让大爷久等。”“用不着惊动锈火的精英,”老板干净利落地把海拉往外一叉,正好让她左耳贴地摔在铁硬的人行道上。
她一节一节地撑了起来,像木匠在打开一把折尺,然后又掸去衣服上的尘土。被捕仿佛只是一个绯色的梦,那个局子远在天边。
一个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站在橱窗前,而离店两码远,就有一位彪形大汉——蛇眼的佣兵。海拉厚着面皮把小耗子该干的那一套恶心勾当一段段表演下去。佣兵在盯着。那被她偷窃的女子只消将手指一招,海拉就等于进安乐岛了。她想象中已经感到了巡捕房的舒适和温暖。年轻的女士却如藤蔓一样缠住了海拉。一拐弯,她甩掉女伴撒腿就走。海拉突然感到一阵恐惧,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紧闭着镇住了她,使她永远也不会被捕呢?
她顺着楼体贫民窟向下走去,因为即使她的家仅仅是辛迪加的破败一角,她仍然有夜深知归的本能。可是,在一个异常幽静的地段,海拉停住了脚步。这里有一座古老的殡仪馆,建筑古雅,不很规整,是有白墙的那种房子。
柔和的灯光透过淡紫色花玻璃窗子映射出来,嘟嘟为了星期天的白事在苦练,刺耳的乐音飘进海拉的耳朵,把她胶着在螺旋形的铁栏杆上。昏暗的灯泡悬在中天,光辉、静穆,车辆与行人都很稀少,檐下的冻雀睡梦中啁啾了几声——这境界一时之间使人想起新城FAC总局边上的墓地。唢呐奏出的哀乐使铁栏杆前的海拉入定了,因为当她在生活中有局长、九十九、夜莺、军团以及安静舒适的居所与够用的钱财时,唢呐对她来说是很熟悉的。海拉这时敏感的心情和殡仪馆的潜移默化会合在一起,使她的灵魂突然起了奇妙的变化。她猛然对她所落入的泥坑感到憎厌。那堕落的时光,低俗的欲望,心灰意懒,才能衰退,动机不良——这一切现在都构成了她的生活内容。

 义勇炭治郎同人文
义勇炭治郎同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