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便我已苏醒,并睁开眼睛,我所看到的还是一片黑暗——至少在我面前都是漆黑的。因此我的其他感官皆被放大,我听得见耳边“窸窸窣窣”的微弱响动,那是成群结队的蚂蚁钻出湿润的土壤,那是泥石下躲藏的马陆探出头来蜿蜒绕行,那是螳螂举起它的镰刀径直豁开我手腕上的皮肉,灰绿色的血液汩汩流淌,又混染上肮脏的尘土,渐渐引来苍蝇,嗡嗡飞着,叮着,它们的屁股全部闪烁斑斓的荧光,和我的手上那滩干涸的血迹一样恶心。苍蝇到处飞,腌臜血污也到处粘,于是在我暂且顾不到的地方,像脚趾头,蜱虫扎进去,潜伏在血肉内,密密麻麻的痛与密密麻麻的痒我反而可以接受,也许是时间过去太久,而我又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久,现在纵然我看不见,我也猜得到是哪种虫子光临我的身体,比如蛞蝓徐徐滑向脖颈儿,留了一抹细长而透明晶亮的粘液挂在锁骨那段凹陷的地方;

蜘蛛的脚步最是轻快,它迅速趋上大腿再循到小腹,雪白的蛛丝缠了一圈接一圈。
蓦地蝴蝶翩翩飞过,翅膀抖落晶莹的鳞粉点缀这幽暗的一隅,美丽的生物本应与我无关,但它却停在我的发梢,触角微摇,静默地“亲吻”我的眼角。
熹微拂晓照醒了我,我的身体依旧不能动,所幸眼珠可以灵活的运转,晨间的阳光格外明媚,我躺在野草丛中,野草高出我的身躯,于是茎叶上的露水滴下来,溅湿了身侧的土壤,土壤里浸满云雾的清香。云雀掠过我的头顶,吟唱喧嚷的颂歌,不知道又在庆祝什么无关紧要的喜事。那根草上有条毛毛虫,慵懒地吸附着叶子,一动不动,而它旁边的瓢虫都咬下一个圆孔啦。起风了,整片旷野沙沙摇曳,风里还有远方的芬芳。



 天使铠抓恶魔守约
天使铠抓恶魔守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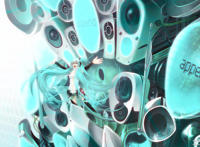




![[月饼梦女]即使天使也是恶魔](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517/164425_41661.jpg)
![[月饼梦女]即使天使也是恶魔](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525/163443_62162.jpg)
![[月饼梦女]即使天使也是恶魔](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13/104438_15954.jpg)
![[月饼梦女]即使天使也是恶魔](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17/154444_7733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