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本水浒(水浒忠义志传明崇祯刘兴我刊本)第四卷——第五卷(29)
”那妇人饮了几盃酒,春心兴发,只管把风情话说。武松亦知,只把头低下。那妇人却把武松肩上捏一下,曰:“叔叔只穿这些衣裳,不冷?”武松也不应。那妇人欲心似火,止遏不住,却筛盃酒来,自吃了一口,剩大半盏,看看武松曰:“你若有心,便吃我这半盏酒。”武松把手泼在地下,睁开两眼叱曰:“武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是那等没人伦的猪狗!嫂嫂这般不知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我眼里认得你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你是嫂嫂!”那妇人红了脸,便收拾盃盘说道:“我自作耍子,不想你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重!”自厨下去了,武松自在房里气忿。有诗为证:
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席间便欲求云雨,反惹都头骂一场。
却说武大挑担归来,到厨下见老婆吊泪,武大曰:“你和谁厮闹来?”妇人曰:“都是你不争气,今日我见武二大雪回来,便安排酒与他吃。他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曰:“我兄弟不是那等人!”便去武松房里叫:“二弟,我和你吃点心。”武松只不做声。依前穿油膀靴,带上毡笠出门去了。武大来问老婆曰:“我叫他不应,只顾走了,不知怎地?”那妇人骂曰:“那厮没脸嘴见你,却走出去。一定叫人来搬行李,你不要留他。”武大曰:“他若搬去,被外人笑。”妇人曰:“他来调戏我,到不怕人笑!你若不与他搬去,还我一纸休书。”只见武松引个土兵,迳入房里收拾行李去了。武大正不知甚事,只得咄咄不乐。
不觉过了数日,知县唤武松曰:“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欲送一担礼物,你去走一遭,回来重重赏你。”武松曰:“恩相差遣,领书就去。”知县大喜。武松便到武大家,拜辞哥嫂曰:“本官差往东京,明日起程,只两个月便回。我不在家,你做买卖迟出早归,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人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又对嫂嫂曰:“嫂嫂你是个精细的人,不必武二多说。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岂不闻:‘离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面通红,指着武松曰:“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你闻言就乱语。”言罢便走入去。武松拜辞时,武大眼中流泪。武松见武大流泪,劝曰:“哥哥,便做不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盘缠欠缺,弟自奉来便了。”武松便带土兵回县来见知县,已自笼箱装载车上,同土兵押车,望东京去了。那武大自从武松说了,每日只做五扇烧饼卖,未晚便回。関上大门,那妇人看了,心下焦燥,指着武大骂曰:
“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便把丧门関上,被人笑耻!”武大曰:“由他咲。我兄弟说的是,省了是非。”武松去了十数日,那妇人也和武大闹了几遭,向后惯了,不以为事。自此,那妇人等武大归时,先自收了帘子,関上大门。
一日,那妇人来门前挂帘子,有一人从帘子边走过。这妇人手里拿竹竿不牢,失手正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正要发作,回过看时,是个妇人,变作笑脸。那妇人笑曰:“奴家时手,官人休怪。”那人曰:“不妨事,娘子请尊便。”却被隔壁王婆见了咲曰:“谁教大官人在屋簷边过,打得好!”那人曰:“是我不是,冲撞娘子,休怪。”去了。原来这人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的财主,在县前开个生熟药铺,自幼好拳棒,近来发迹,满县人都怕他,覆姓西门名庆,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那西门庆复转入王婆茶坊里坐下,问曰:“那妇人是谁妻小?”王婆曰:“街上卖烧饼的武大郎妻子。”西门庆咲曰:“莫不是三寸丁谷树皮?”王婆曰:“正是了。”西门庆曰:“好一块羊肉,怎的落在狗口里?”王婆曰:“自古道:‘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妻每伴拙夫眠。’”言罢,西门庆辞去。次日,又来王婆店里,取出一两银子,递与王婆曰:
泼贱操心太不良,贪淫无耻坏纲常。席间便欲求云雨,反惹都头骂一场。
却说武大挑担归来,到厨下见老婆吊泪,武大曰:“你和谁厮闹来?”妇人曰:“都是你不争气,今日我见武二大雪回来,便安排酒与他吃。他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曰:“我兄弟不是那等人!”便去武松房里叫:“二弟,我和你吃点心。”武松只不做声。依前穿油膀靴,带上毡笠出门去了。武大来问老婆曰:“我叫他不应,只顾走了,不知怎地?”那妇人骂曰:“那厮没脸嘴见你,却走出去。一定叫人来搬行李,你不要留他。”武大曰:“他若搬去,被外人笑。”妇人曰:“他来调戏我,到不怕人笑!你若不与他搬去,还我一纸休书。”只见武松引个土兵,迳入房里收拾行李去了。武大正不知甚事,只得咄咄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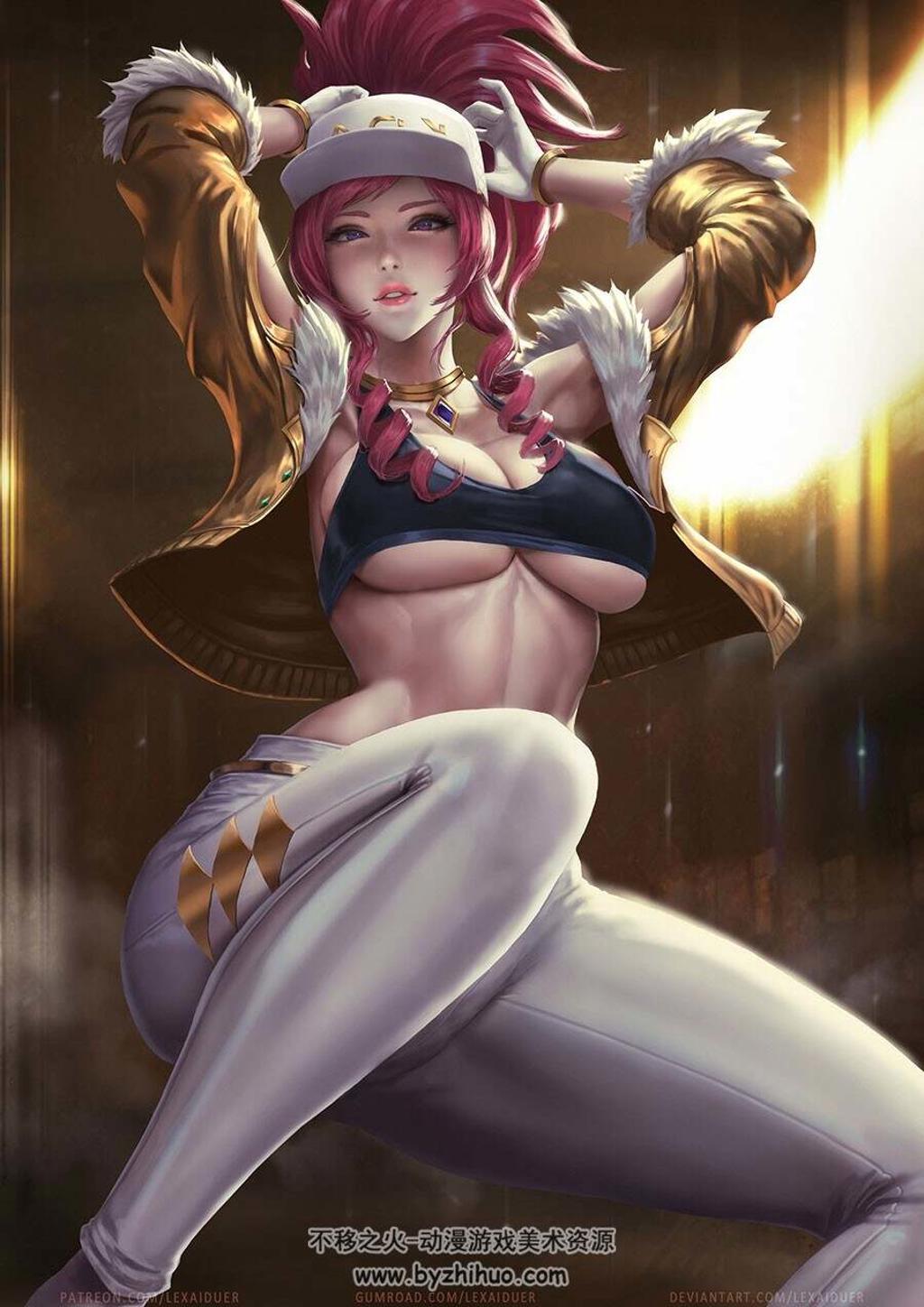
不觉过了数日,知县唤武松曰:“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欲送一担礼物,你去走一遭,回来重重赏你。”武松曰:“恩相差遣,领书就去。”知县大喜。武松便到武大家,拜辞哥嫂曰:“本官差往东京,明日起程,只两个月便回。我不在家,你做买卖迟出早归,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人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又对嫂嫂曰:“嫂嫂你是个精细的人,不必武二多说。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岂不闻:‘离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面通红,指着武松曰:“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你闻言就乱语。”言罢便走入去。武松拜辞时,武大眼中流泪。武松见武大流泪,劝曰:“哥哥,便做不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盘缠欠缺,弟自奉来便了。”武松便带土兵回县来见知县,已自笼箱装载车上,同土兵押车,望东京去了。那武大自从武松说了,每日只做五扇烧饼卖,未晚便回。関上大门,那妇人看了,心下焦燥,指着武大骂曰:
“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便把丧门関上,被人笑耻!”武大曰:“由他咲。我兄弟说的是,省了是非。”武松去了十数日,那妇人也和武大闹了几遭,向后惯了,不以为事。自此,那妇人等武大归时,先自收了帘子,関上大门。
一日,那妇人来门前挂帘子,有一人从帘子边走过。这妇人手里拿竹竿不牢,失手正打在那人头巾上。那人正要发作,回过看时,是个妇人,变作笑脸。那妇人笑曰:“奴家时手,官人休怪。”那人曰:“不妨事,娘子请尊便。”却被隔壁王婆见了咲曰:“谁教大官人在屋簷边过,打得好!”那人曰:“是我不是,冲撞娘子,休怪。”去了。原来这人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的财主,在县前开个生熟药铺,自幼好拳棒,近来发迹,满县人都怕他,覆姓西门名庆,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那西门庆复转入王婆茶坊里坐下,问曰:“那妇人是谁妻小?”王婆曰:“街上卖烧饼的武大郎妻子。”西门庆咲曰:“莫不是三寸丁谷树皮?”王婆曰:“正是了。”西门庆曰:“好一块羊肉,怎的落在狗口里?”王婆曰:“自古道:‘骏马常驮痴汉走,巧妻每伴拙夫眠。’”言罢,西门庆辞去。次日,又来王婆店里,取出一两银子,递与王婆曰:
 吾师第三卷挨打
吾师第三卷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