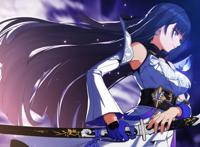于圣殿下(3)
“感谢您的大度。”我有些手足无措,坐立不安的模样活像只蠢笨的鹌鹑,“我会尽量表现得不那么像个虔诚的信徒……我是说,在您面前的话……”
“历史。”西参古教授用他修长的,长满荧黄色斑点的第三指——亦即最强壮的那根——敲在他身前用原木雕琢的巨大书桌上,“夏伽,这才是你拜访我的目的。”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人类总会为历史着迷,即便那属于另一个种族。
做为少数以锡族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参古教授,其长篇论文《从政治审视:锡族部落制度沿革与变化》以精准沉静的笔调详实又动人地描绘了在人类登陆前这个不羁狂野的种族于社会体制上的合乎逻辑之演变发展,尽管仍有不少嫉妒得眼眶发红的学者认为教授本人的锡族身份为研究过程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那一年学界的最高荣誉以实马理奖依然在压倒性的优势下被授予西参古团队,也是在那个颁奖礼上,教授被神尊在人世间的代行者赐以象征“智慧”的圣血披肩。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那是所有蒙福的圣殿子民渴求一生的无上冠冕。
“夏伽?”教授看出我心不在焉,却不知我正沉湎于他过往辉煌的回忆。
“抱歉,西参古教授。”我颇为狼狈地回过神,并努力抑制住想要祷告的双手,“我走神了。”
“放松点,锡族人没那么可怕。”教授很宽容,甚至朝我开了一个玩笑,然而足足三十秒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挤出个难看又尴尬的别扭微笑。
是的,人类在过去惊叹于锡族高达十三英尺的雄健体魄与扁平额头上那枚锋利狭长的单目,这给了原住民某种难以言喻的威严与庄重,以至于第一批人类移民曾以为对方才是天父真正钟爱的造物。
“我太迟钝了,教授。”我为自己的愚笨致歉。
“或许我们该谈谈正事?”西参古教授满是善意朝我调侃,并没有在意面前这个年轻学生手足无措的稚嫩表现。他俯身从书桌下方抽屉中取出一封保存完好,干净工整的信纸,那是我誊写了五遍后才勉强做到的,“你在信里写希望把锡族历史作为毕业论文方向,所以才想上门向我讨教。”
“您说得不错。”过度的焦虑使我将弯曲的膝盖并拢,坚硬的骨头硌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选择,基于锡族的特殊性与您在此领域的权威,学界一致认为原住民历史已经盖棺定论,所以我才想到亲自拜访您,以期能够在课题上获得一些可供研究的新方向……”
“历史。”西参古教授用他修长的,长满荧黄色斑点的第三指——亦即最强壮的那根——敲在他身前用原木雕琢的巨大书桌上,“夏伽,这才是你拜访我的目的。”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人类总会为历史着迷,即便那属于另一个种族。
做为少数以锡族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参古教授,其长篇论文《从政治审视:锡族部落制度沿革与变化》以精准沉静的笔调详实又动人地描绘了在人类登陆前这个不羁狂野的种族于社会体制上的合乎逻辑之演变发展,尽管仍有不少嫉妒得眼眶发红的学者认为教授本人的锡族身份为研究过程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那一年学界的最高荣誉以实马理奖依然在压倒性的优势下被授予西参古团队,也是在那个颁奖礼上,教授被神尊在人世间的代行者赐以象征“智慧”的圣血披肩。
“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那是所有蒙福的圣殿子民渴求一生的无上冠冕。

“夏伽?”教授看出我心不在焉,却不知我正沉湎于他过往辉煌的回忆。
“抱歉,西参古教授。”我颇为狼狈地回过神,并努力抑制住想要祷告的双手,“我走神了。”
“放松点,锡族人没那么可怕。”教授很宽容,甚至朝我开了一个玩笑,然而足足三十秒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并挤出个难看又尴尬的别扭微笑。
是的,人类在过去惊叹于锡族高达十三英尺的雄健体魄与扁平额头上那枚锋利狭长的单目,这给了原住民某种难以言喻的威严与庄重,以至于第一批人类移民曾以为对方才是天父真正钟爱的造物。
“我太迟钝了,教授。”我为自己的愚笨致歉。
“或许我们该谈谈正事?”西参古教授满是善意朝我调侃,并没有在意面前这个年轻学生手足无措的稚嫩表现。他俯身从书桌下方抽屉中取出一封保存完好,干净工整的信纸,那是我誊写了五遍后才勉强做到的,“你在信里写希望把锡族历史作为毕业论文方向,所以才想上门向我讨教。”
“您说得不错。”过度的焦虑使我将弯曲的膝盖并拢,坚硬的骨头硌在一起,“我明白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选择,基于锡族的特殊性与您在此领域的权威,学界一致认为原住民历史已经盖棺定论,所以我才想到亲自拜访您,以期能够在课题上获得一些可供研究的新方向……”

 公主殿下gl
公主殿下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