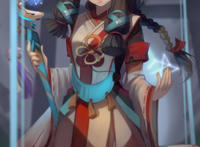匪弃·上(2)
林弃闭眼。
“……”
床榻发出一声嘶哑的悲鸣,似是困兽的苟延残喘。
低低的喘息声落在耳边,林弃只是安静的,任那人将自己揉入怀里,近乎要把骨头勒断,融入血肉。
相比起他的赤裸,匪之的衣物依旧整洁,上衣袋中的怀表硌在他的脊骨上,冰得四肢麻木。
连心脏都快麻木了。
军营里来了位…客人。
对匪之来说并不陌生,对林弃而言也是——不过他无法离开地下室,故也见不到这位客人。
“大哥怎么有空到这边来。”匪之玩着一柄折叠小刀,面上带着些许孩童的纯真。
水一看着他,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领导者。
他斟酌半晌,开口道:“我听说你…林弃他…”
匪之笑容不变,薄如蝉翼的刀刃压着脆弱的手腕,他满不在乎地说道:“我有权利支配我的战俘。”说着,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转动,目光落在水一无名指上的素戒上,“就像你杀了他,辞去官职一样,那是你的选择。唔…我可舍不得他去死。”
被戳中痛点的水一脸色有些发白,他下意识地去碰指上的银戒,被体温捂热了,仿佛那人掌心的温度。
匪之不去戳穿他的失态,他好似对刀的兴趣更浓着,在五指间转出了花。
“所以你就把他囚禁起来,把他的骄傲折碎?”水一深吸一口气,“匪之,那只会让他更恨你。”
“恨选比爱要来得深刻得多,不是吗?”匪之打断他的话,眼眸低垂,“大哥,他什么都没有了,若是连恨也不恨了,他真的会去死的…”
水一一时看不透他那是什么情绪,气氛一下子凝固了下来。
“如果,有一天,他放弃了…”
“不会。”匪之笃定,“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他不会。…”刀刃在掌心划了深深的一道口子,鲜血如毒蛇蜿蜒向下,舔脏了一丝不苟的白衬衫。
水一看得心惊胆战。
“如果哪一天他选择死亡,一定会把我也拖下地狱的。”他咬着雪白的纱布,一圈一圈缠在伤口上,鲜血很快渗透到最外层,他也不在意。
这场谈话算是不欢而散,匪之并无所谓,灭国之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善后,他的大半精力扑在林弃身上,剩下的全部献给帝国,实在是无力再去维持一些以前的关系了。
“将军,他…”有下属敲了敲门。
匪之看到他欲言又止,皱眉:“又不吃饭?”
“是,一口都没动。”下属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去重新做一份,我拿过去。”他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挥手让下属退下。
“……”
床榻发出一声嘶哑的悲鸣,似是困兽的苟延残喘。
低低的喘息声落在耳边,林弃只是安静的,任那人将自己揉入怀里,近乎要把骨头勒断,融入血肉。
相比起他的赤裸,匪之的衣物依旧整洁,上衣袋中的怀表硌在他的脊骨上,冰得四肢麻木。
连心脏都快麻木了。
军营里来了位…客人。
对匪之来说并不陌生,对林弃而言也是——不过他无法离开地下室,故也见不到这位客人。
“大哥怎么有空到这边来。”匪之玩着一柄折叠小刀,面上带着些许孩童的纯真。
水一看着他,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领导者。
他斟酌半晌,开口道:“我听说你…林弃他…”
匪之笑容不变,薄如蝉翼的刀刃压着脆弱的手腕,他满不在乎地说道:“我有权利支配我的战俘。”说着,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转动,目光落在水一无名指上的素戒上,“就像你杀了他,辞去官职一样,那是你的选择。唔…我可舍不得他去死。”
被戳中痛点的水一脸色有些发白,他下意识地去碰指上的银戒,被体温捂热了,仿佛那人掌心的温度。
匪之不去戳穿他的失态,他好似对刀的兴趣更浓着,在五指间转出了花。

“所以你就把他囚禁起来,把他的骄傲折碎?”水一深吸一口气,“匪之,那只会让他更恨你。”
“恨选比爱要来得深刻得多,不是吗?”匪之打断他的话,眼眸低垂,“大哥,他什么都没有了,若是连恨也不恨了,他真的会去死的…”
水一一时看不透他那是什么情绪,气氛一下子凝固了下来。
“如果,有一天,他放弃了…”
“不会。”匪之笃定,“我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他不会。…”刀刃在掌心划了深深的一道口子,鲜血如毒蛇蜿蜒向下,舔脏了一丝不苟的白衬衫。
水一看得心惊胆战。
“如果哪一天他选择死亡,一定会把我也拖下地狱的。”他咬着雪白的纱布,一圈一圈缠在伤口上,鲜血很快渗透到最外层,他也不在意。
这场谈话算是不欢而散,匪之并无所谓,灭国之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善后,他的大半精力扑在林弃身上,剩下的全部献给帝国,实在是无力再去维持一些以前的关系了。
“将军,他…”有下属敲了敲门。
匪之看到他欲言又止,皱眉:“又不吃饭?”
“是,一口都没动。”下属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去重新做一份,我拿过去。”他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挥手让下属退下。

 舰娘嫌弃指挥官
舰娘嫌弃指挥官



![[国风]匪妄](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54628_79742.jpg)
![[国风]匪妄](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62600_19281.jpg)
![[国风]匪妄](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024/140942_45871.jpg)
![[国风]匪妄](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024/162142_938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