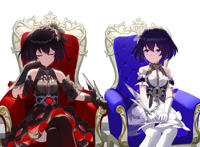宫墙柳•蓝湛篇【羡忘】(中)(7)
“他挺好的……对我,挺好的。”
若是问我与魏婴如何相处,那我或许能找到个荒唐却十分贴切的词,叫做“相濡以沫”。可若单问魏婴是个怎样的人,我在脑海里走马观花回望了这么些年的点点滴滴,竟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细述他的好。太多了,可都太苍白,它是我心里的一种感觉,一种,旁人怎么会懂,我亦不愿旁人能懂的感觉。
母妃这一问,于我而言,醍醐灌顶。
魏二十五年七月七,我与魏婴大婚。
陛下“怜惜”,免我受奔波之苦,准我从咸安宫启程,落轿羡王府。
半月前,我父王也来了云梦。门扉一阖,他便黑了一张脸,一脚踢在聘礼箱子上。箱子是死物,不会疼的,这踢出多大动静便是在跟自己较多大的劲儿。母妃惶恐又心疼,垂首上前欲扶我父王坐下,眼泪弄花了她今日特地薄施的粉黛。父王牵过她的手,也拉过我的,我们一家人,紧紧依靠在一起,头抵着头。
若是问我与魏婴如何相处,那我或许能找到个荒唐却十分贴切的词,叫做“相濡以沫”。可若单问魏婴是个怎样的人,我在脑海里走马观花回望了这么些年的点点滴滴,竟实在想不出什么可以细述他的好。太多了,可都太苍白,它是我心里的一种感觉,一种,旁人怎么会懂,我亦不愿旁人能懂的感觉。

母妃这一问,于我而言,醍醐灌顶。
魏二十五年七月七,我与魏婴大婚。
陛下“怜惜”,免我受奔波之苦,准我从咸安宫启程,落轿羡王府。
半月前,我父王也来了云梦。门扉一阖,他便黑了一张脸,一脚踢在聘礼箱子上。箱子是死物,不会疼的,这踢出多大动静便是在跟自己较多大的劲儿。母妃惶恐又心疼,垂首上前欲扶我父王坐下,眼泪弄花了她今日特地薄施的粉黛。父王牵过她的手,也拉过我的,我们一家人,紧紧依靠在一起,头抵着头。

 忘羡暴怒蓝湛篇
忘羡暴怒蓝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