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
可她似乎没有让我回应的意思,看我一眼便重新看向电视,我松口气,可心中烦闷感觉愈加剧烈,难以排解——准确来说当下无法排解,毕竟我不清楚她话语中的真实含义,也不明白她说出这话的用意。
为了搞懂眼下这一切,第二天我便早早出门,在上班时间之前赶到罗德岛在维多利亚的办事处,找到正准备上班的干员们,一一询问同一个问题。
“你会怎么对待过期的罐头?“我问。
“丢掉啊。“玫兰莎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当时是丢掉啦,不然怎么处理?“雪雉不假思索地回答。
“丢掉啊,过期的食物可不能吃。“芙蓉眨眨眼睛,关掉了一旁的炉子,炉子上放了口锅,锅里装着难以分辨其成分的糊状物。
除了她们三个,我又问了问十来个干员,得到的回答无不相同。之后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无需再问,丢掉过期食物无疑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也没有心情再问,在询问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她话中的含义,尽管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我心中难免还是生起些许悲哀之情。
因为可能在她眼里,现在的我和过期罐头,是一样的。
自那天以后又过了三日,极为奇异的三日,至于为何会用奇异来形容,是因为我无法用自己知晓的任何词语来描述那72小时的时间,即使是奇异这一用处颇多的词语,也无法准确形容这段时间的性质。
那三天里,她的行为与前些日子——发生改变后的日子——几乎无异。我也一样,从表面上,依旧是照常上班,照常吃喝,照常排泄,照常休息。可在我的眼里,周围目力所及的一切似乎都被蒙上一层厚膜,密不透风,仿佛有无形力量将我与世界一分为二;极其干净利落且彻底的分割,甚至没让我反应过来,连抗议或者呼救的机会都没留下。
我尝试挣脱,可那将我与世界分开的障壁坚韧异常,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于是放弃挣扎,尝试让自己与这障壁共存;可它有着特殊的过滤能力,在这三天里,任何人的话语表情或是肢体动作,以及其他任何能够传达信息的“什么”,在得以被我理解之前,似乎都被这障壁滤去其真正含义;本该传入耳中的话语变成毫无意义的字符组合,含义丰富的面部表情也变成五官的无规律移动,就连那些习以为常的肢体动作,都变成了无法理解的肢体移动。毫无疑问,我已陷入难以与任何人正常交流的窘境。
而我最终无法忍受这种窘境,于是在第七十二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在午夜零点冲出家门,沿着灯光微弱的小镇街道,缓缓前行。
小镇的路灯多年未换,灯泡亮度大不如前,只能照亮方圆三四米空间。我踱到路灯旁,背靠灯柱坐下,打算稍作休息。不知是不是心情低落的缘故,我忽然感觉周遭的微弱灯光温暖无比,这光虽弱,却毫无阻碍地穿过那厚膜,给我真切的感受。我有些鼻酸,在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之后,这微弱光芒是唯一给予我真切感受的东西。
为了搞懂眼下这一切,第二天我便早早出门,在上班时间之前赶到罗德岛在维多利亚的办事处,找到正准备上班的干员们,一一询问同一个问题。
“你会怎么对待过期的罐头?“我问。
“丢掉啊。“玫兰莎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当时是丢掉啦,不然怎么处理?“雪雉不假思索地回答。
“丢掉啊,过期的食物可不能吃。“芙蓉眨眨眼睛,关掉了一旁的炉子,炉子上放了口锅,锅里装着难以分辨其成分的糊状物。
除了她们三个,我又问了问十来个干员,得到的回答无不相同。之后我没有继续问下去,无需再问,丢掉过期食物无疑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也没有心情再问,在询问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她话中的含义,尽管不敢百分之百确定,我心中难免还是生起些许悲哀之情。
因为可能在她眼里,现在的我和过期罐头,是一样的。
自那天以后又过了三日,极为奇异的三日,至于为何会用奇异来形容,是因为我无法用自己知晓的任何词语来描述那72小时的时间,即使是奇异这一用处颇多的词语,也无法准确形容这段时间的性质。

那三天里,她的行为与前些日子——发生改变后的日子——几乎无异。我也一样,从表面上,依旧是照常上班,照常吃喝,照常排泄,照常休息。可在我的眼里,周围目力所及的一切似乎都被蒙上一层厚膜,密不透风,仿佛有无形力量将我与世界一分为二;极其干净利落且彻底的分割,甚至没让我反应过来,连抗议或者呼救的机会都没留下。
我尝试挣脱,可那将我与世界分开的障壁坚韧异常,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于是放弃挣扎,尝试让自己与这障壁共存;可它有着特殊的过滤能力,在这三天里,任何人的话语表情或是肢体动作,以及其他任何能够传达信息的“什么”,在得以被我理解之前,似乎都被这障壁滤去其真正含义;本该传入耳中的话语变成毫无意义的字符组合,含义丰富的面部表情也变成五官的无规律移动,就连那些习以为常的肢体动作,都变成了无法理解的肢体移动。毫无疑问,我已陷入难以与任何人正常交流的窘境。
而我最终无法忍受这种窘境,于是在第七十二个小时过去以后,我在午夜零点冲出家门,沿着灯光微弱的小镇街道,缓缓前行。
小镇的路灯多年未换,灯泡亮度大不如前,只能照亮方圆三四米空间。我踱到路灯旁,背靠灯柱坐下,打算稍作休息。不知是不是心情低落的缘故,我忽然感觉周遭的微弱灯光温暖无比,这光虽弱,却毫无阻碍地穿过那厚膜,给我真切的感受。我有些鼻酸,在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系之后,这微弱光芒是唯一给予我真切感受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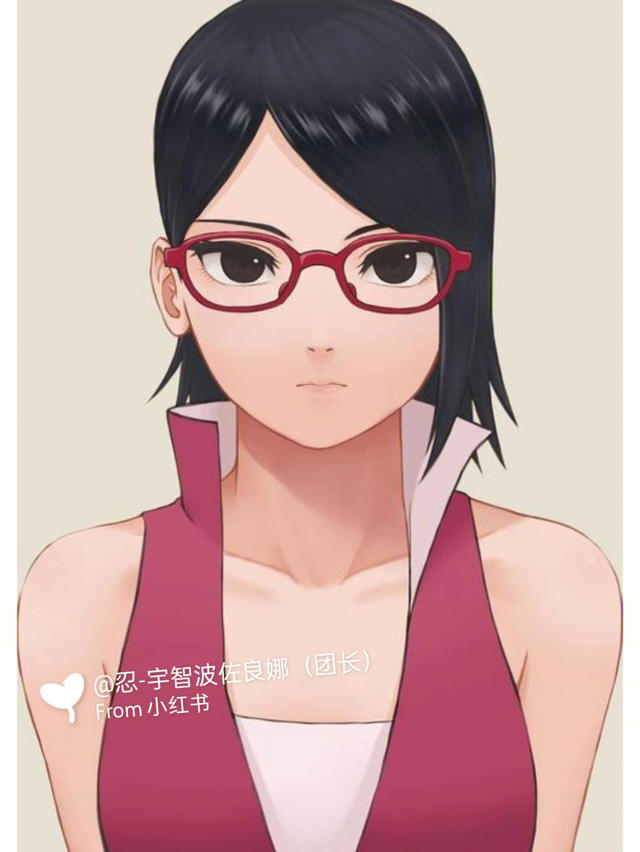
 all澄换命5
all澄换命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