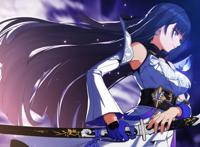掉下来的星星(2)
次数多了,一向恃才而骄的调酒师难得开口问她,大概也是出于对凌肖喜欢的女孩的好奇,“会调?”
青澈不说自己会,也不摇头说不会,很有分寸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会一点。”
这么模棱两可的答案,调酒师倒是起了兴趣。倒了好几杯不重样的酒给她,又上了专业的调酒器。
小女孩也不推脱,每杯酒都倒出一点尝了尝味道。
调酒师把雪克壶递给她,想用夹冰器打打下手,小丫头摆摆手示意不要,想直接注入酒杯配制。
Adam和凌肖一直在舞台下看着这边的动静。看青澈用直接注入法配酒,即便对青澈挺有好感,Adam还是在心中哀叹,这小祖宗怕是要糟蹋了那几杯不错的酒。
青澈调酒的样子和平时文文弱弱的形象十分不符,像凌肖弹贝斯的样子,豪放而肆意。拿了酒就“哗”地往调酒杯里倒,倒多少酒倒什么酒全靠手感,好似小孩子给自己沏糖水,糖多了加水,水多了加糖。
调酒师还没心疼他的酒呢,Adam就替他心疼的不得了了,双手捂着眼睛数着数,让凌肖在青澈调完酒以后告诉他。凌肖看得正出神,用手肘捣了捣Adam,敷衍地说知道了知道了,Adam虽然对凌肖的态度十分伤心,但还是继续数自己的一二三四五。
酒吧匙在调制杯里搅了搅,蓝色的液体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种发暖的紫色,气泡还在咕咕地往上游,好像一条条小鱼。青澈舀出一点抿了抿,点点头,语气松快了许多,“好了。”
“调的不错,”调酒师少有地给面子鼓了鼓掌,“叫什么?”
青澈有些缓慢地眨了下眼,思考了一会,大概是从蓝紫色的酒联想到了某人的头发,慢慢开口:“含笑,叫含笑。”
“含笑花什么色的?”酒保试探性地询问道。把眼捂得死死的Adam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迭声叫着凌肖的名字问他怎么样,凌肖一句没吭,旁边的Jensen惊呼了声"肖仔”。Adam把手移开一看,青澈整个人就像根面条似的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凌肖伸手虚虚地护着她,手指在她额头上揉了揉,看样子是刚才磕到吧台上了。
青澈不说自己会,也不摇头说不会,很有分寸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会一点。”
这么模棱两可的答案,调酒师倒是起了兴趣。倒了好几杯不重样的酒给她,又上了专业的调酒器。
小女孩也不推脱,每杯酒都倒出一点尝了尝味道。
调酒师把雪克壶递给她,想用夹冰器打打下手,小丫头摆摆手示意不要,想直接注入酒杯配制。
Adam和凌肖一直在舞台下看着这边的动静。看青澈用直接注入法配酒,即便对青澈挺有好感,Adam还是在心中哀叹,这小祖宗怕是要糟蹋了那几杯不错的酒。
青澈调酒的样子和平时文文弱弱的形象十分不符,像凌肖弹贝斯的样子,豪放而肆意。拿了酒就“哗”地往调酒杯里倒,倒多少酒倒什么酒全靠手感,好似小孩子给自己沏糖水,糖多了加水,水多了加糖。

调酒师还没心疼他的酒呢,Adam就替他心疼的不得了了,双手捂着眼睛数着数,让凌肖在青澈调完酒以后告诉他。凌肖看得正出神,用手肘捣了捣Adam,敷衍地说知道了知道了,Adam虽然对凌肖的态度十分伤心,但还是继续数自己的一二三四五。
酒吧匙在调制杯里搅了搅,蓝色的液体在灯光下反射出一种发暖的紫色,气泡还在咕咕地往上游,好像一条条小鱼。青澈舀出一点抿了抿,点点头,语气松快了许多,“好了。”
“调的不错,”调酒师少有地给面子鼓了鼓掌,“叫什么?”
青澈有些缓慢地眨了下眼,思考了一会,大概是从蓝紫色的酒联想到了某人的头发,慢慢开口:“含笑,叫含笑。”
“含笑花什么色的?”酒保试探性地询问道。把眼捂得死死的Adam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迭声叫着凌肖的名字问他怎么样,凌肖一句没吭,旁边的Jensen惊呼了声"肖仔”。Adam把手移开一看,青澈整个人就像根面条似的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凌肖伸手虚虚地护着她,手指在她额头上揉了揉,看样子是刚才磕到吧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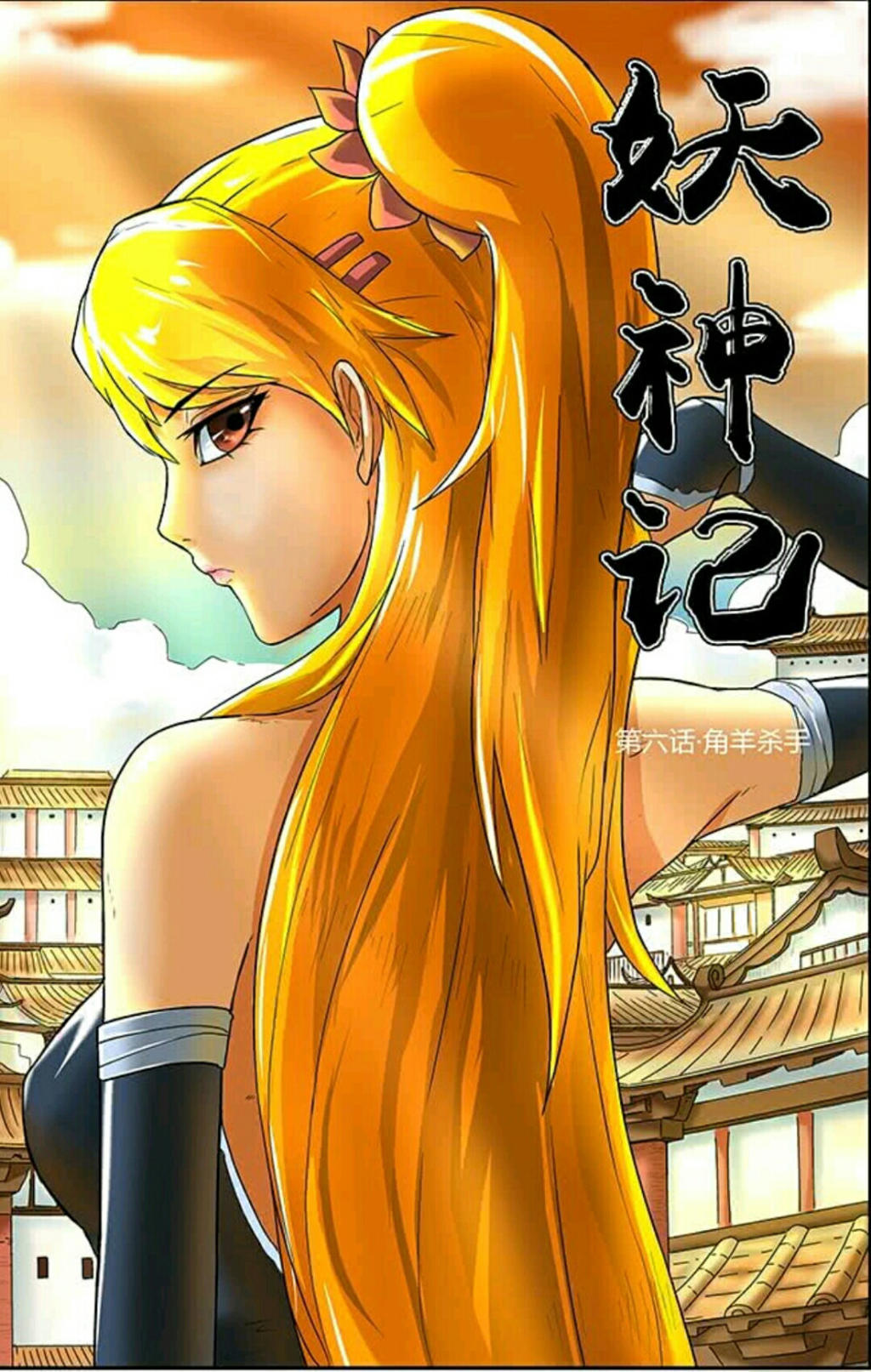
 堵好了一滴也别流出来我下星期
堵好了一滴也别流出来我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