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驾光临(15)
这些简单却深刻的话启发了诺尔,他决定再一次把自己的世界变回一片混乱,按照这句浮空的话语去做。
(六)
孩子们依然下落不明!
身心日渐消极的身体状况无法保证下一次寻找孩子们的体力,而弄伤她手臂和颈部的丈夫无颜面对居民们的眼光,在一声道歉都没有传达的情况下就一直把自己封在书房里,不愿意出来。
她想过要离开威尔顿一家,可是那个来自不知何处的声音直接传进了耳廓:
“你一定想要摆脱这一切吧——那艾玛和玛德琳也不顾着把?”
“她们是我的孩子,我不管我是不是她们的亲生母亲!”丽兹只能不断地在心里暗示。
她走到孩子们原来的卧室,卧室的床铺依然是光秃秃的,毫无任何人的踪迹。在给教师和女仆放假前,房间已经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等待着在外面开心了一整天的女孩们回归安心入睡。
“我傻啊,我真傻。当初为了要过个好生活、与众不同的后半生,我把自己的身心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威尔顿身上。我在他眼里只要不陪他拜弘治教,就是位淫秽下流、卑鄙无耻、无恶不休的女人。许多分钟以前,许多小时以后,许多天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就是个失败的人。可我不敢承认!哦,可怜我吧,我是个可笑的灵魂,居然要在女仆方面死死地展示我是他的妻子!我为了妻子的脸面一直忍气吞声地迁就他,直到我的艾玛和玛德琳全部逃跑了!我给她们好吃的、好喝的,穿好看的,让她们在威尔顿家里享受没有流浪之苦的天伦之乐,可我毁了她们!我不敢说!我毁了我的孩子们!”
“我已经着魔了,我的丈夫着魔了!整个屋子都已经着魔了!我已经成了被上紧发条的玩偶!要是我的孩子们还在,我现在就要告诉她们,我们的向恶的命运已经挣脱了所有神灵的囚禁,它在我与诺尔结合的时候已经微微蠢动的轻微响动我就听见了。我听见了动静,许多天以前,许多天以前。但我不敢,我不敢说!可现在,今天晚上,艾玛,玛德琳!那轮椅的铿锵落地,那不断渗透天花板的血液,那六幅会动会响的油画!正是它破巢而出的前兆吗?还不如说是它灵柩的破裂声,囚禁身心的铁链摩擦声,她在地下仆人间的挣扎声!我现在能逃得出去吗?我听信了媒灼之言,跟那个着魔丈夫结婚,享用他的钱财,却陷入永恒的米诺斯迷宫,住进了这着魔的异邦小镇!我的女孩们全部消失在了这非人之地!难道谁也不相信我丈夫、原心公馆,还有拉舍尔小镇都是一群孽障吗?我活到现在知晓了命运的荒谬,难道非要达到这种境地我才能如梦初醒吗?
那个声音天天都在纠缠我,还有我的丈夫,甚至我女孩们!”念叨到这儿她突然一跃而起,把嗓音提到尖叫的程度,仿佛她正在做垂死的挣扎,“疯狂的你啊,你永远不得永生!”
似乎她那声具有超凡力量的呼叫具有一股魔力,随着她那声呼叫,她死死地抓住床栏,那扇陈旧的木门似乎被风吹得缓缓张开,但是,门外果真站着身披白袍的诺尔凛然的身影。他那白色的袍衣上全是华南虎锋利抓痕留下的大洞,依然健壮的身子浑身都是疯狂自残后留下的伤口和脓液,双眼完全泛白。
(六)
孩子们依然下落不明!
身心日渐消极的身体状况无法保证下一次寻找孩子们的体力,而弄伤她手臂和颈部的丈夫无颜面对居民们的眼光,在一声道歉都没有传达的情况下就一直把自己封在书房里,不愿意出来。
她想过要离开威尔顿一家,可是那个来自不知何处的声音直接传进了耳廓:
“你一定想要摆脱这一切吧——那艾玛和玛德琳也不顾着把?”
“她们是我的孩子,我不管我是不是她们的亲生母亲!”丽兹只能不断地在心里暗示。
她走到孩子们原来的卧室,卧室的床铺依然是光秃秃的,毫无任何人的踪迹。在给教师和女仆放假前,房间已经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等待着在外面开心了一整天的女孩们回归安心入睡。
“我傻啊,我真傻。当初为了要过个好生活、与众不同的后半生,我把自己的身心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威尔顿身上。我在他眼里只要不陪他拜弘治教,就是位淫秽下流、卑鄙无耻、无恶不休的女人。许多分钟以前,许多小时以后,许多天以前我就知道自己就是个失败的人。可我不敢承认!哦,可怜我吧,我是个可笑的灵魂,居然要在女仆方面死死地展示我是他的妻子!我为了妻子的脸面一直忍气吞声地迁就他,直到我的艾玛和玛德琳全部逃跑了!我给她们好吃的、好喝的,穿好看的,让她们在威尔顿家里享受没有流浪之苦的天伦之乐,可我毁了她们!我不敢说!我毁了我的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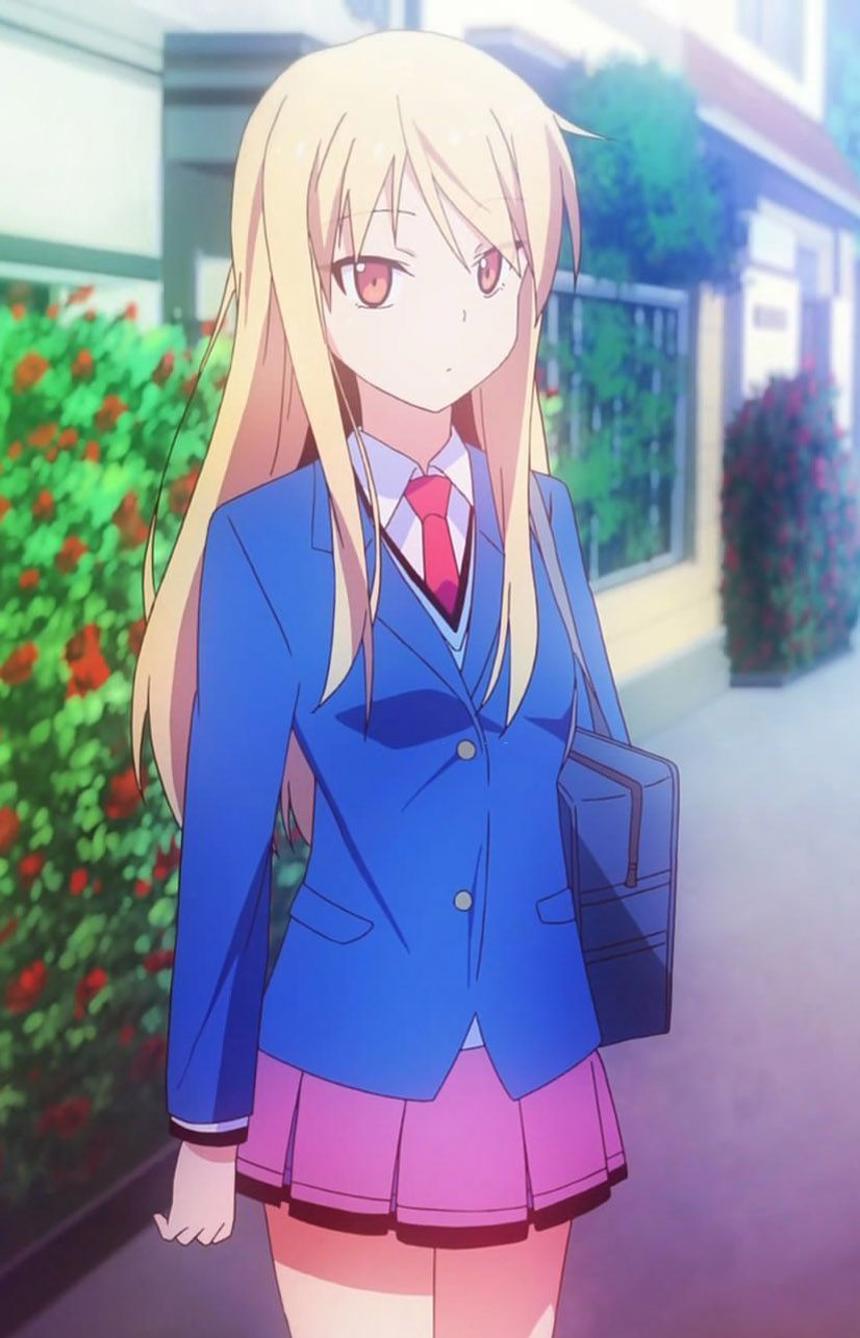
“我已经着魔了,我的丈夫着魔了!整个屋子都已经着魔了!我已经成了被上紧发条的玩偶!要是我的孩子们还在,我现在就要告诉她们,我们的向恶的命运已经挣脱了所有神灵的囚禁,它在我与诺尔结合的时候已经微微蠢动的轻微响动我就听见了。我听见了动静,许多天以前,许多天以前。但我不敢,我不敢说!可现在,今天晚上,艾玛,玛德琳!那轮椅的铿锵落地,那不断渗透天花板的血液,那六幅会动会响的油画!正是它破巢而出的前兆吗?还不如说是它灵柩的破裂声,囚禁身心的铁链摩擦声,她在地下仆人间的挣扎声!我现在能逃得出去吗?我听信了媒灼之言,跟那个着魔丈夫结婚,享用他的钱财,却陷入永恒的米诺斯迷宫,住进了这着魔的异邦小镇!我的女孩们全部消失在了这非人之地!难道谁也不相信我丈夫、原心公馆,还有拉舍尔小镇都是一群孽障吗?我活到现在知晓了命运的荒谬,难道非要达到这种境地我才能如梦初醒吗?
那个声音天天都在纠缠我,还有我的丈夫,甚至我女孩们!”念叨到这儿她突然一跃而起,把嗓音提到尖叫的程度,仿佛她正在做垂死的挣扎,“疯狂的你啊,你永远不得永生!”
似乎她那声具有超凡力量的呼叫具有一股魔力,随着她那声呼叫,她死死地抓住床栏,那扇陈旧的木门似乎被风吹得缓缓张开,但是,门外果真站着身披白袍的诺尔凛然的身影。他那白色的袍衣上全是华南虎锋利抓痕留下的大洞,依然健壮的身子浑身都是疯狂自残后留下的伤口和脓液,双眼完全泛白。
 明日方舟博士x临光病娇
明日方舟博士x临光病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