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Umy」七月病(5)
咩栗愣了一会,觉得心跳也被拆解变成新的律动周期,她有些懊恼地趴上桌子,听见笔尖书写在阳光里的刷刷声,教室正前方的钟摆仍在机械地来回,她看向分针,离考试结束还有二十七分钟。
咩栗感到不甘,她开始购买理科的教辅,同桌咬着酸奶吸管,看她的眼神活像见鬼。她问咩栗:你怎么了?咩栗瘪嘴,说我也想学理科。同桌倒吸一口气,说你疯了。
咩栗开始熬夜,终于在第三周的某个深夜被偏铝酸钠干趴。
她难受了一整晚,从第二天开始把物化生的教材全塞进抽屉最底下吃灰。
咩栗像一滚水,沸腾过后最终也冷下来。她看着呜米,总是突然觉得心脏溺水一阵子,挣扎着又醒过来呼吸了。她偶尔做梦,梦见一些呜米的碎片,比如最开始时她望过来的一眼,她的作业,她罩在自己身上的外衣...还有她们渐行渐远的未来。
但最后咩栗全都沉默着接受了。
高一时她仍然常常生病,生一些名字拗口念不干脆的病,她时常请假、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零零散散地读博尔赫斯的诗,然后领药回家,那些生僻字全都窸窸窣窣地混在一起,她也因此连味觉都曾败坏三分。可咩栗望着她的背影,嗓间默念着青绿色的年纪。
——十六、十六啊。唯一能和她仰望同一片天空的、蝴蝶般的十六岁啊。
她闭上眼,仍觉得比糖甜。
分别的时候恰是流泪的天气,咩栗什么都不想地站着,十六骨的晴雨伞挂在她的手腕上。下午她还在这里听了最后一节地理课,晚修就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她有些出神,只隐约记得自己被分去十七班,所幸还和同桌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团潮湿的空气,没有实质。呜米从外面跑进来,浑身淋得湿透,咩栗匆匆看了她一眼,以为这就是最后了。
而几秒后呜米拉住她的手腕,叫她。
咩栗。
咩栗略显错愕地看她,先是看到呜米手腕上的那根红绳,从袖筒里露出来,红色亮得扎眼,她再抬头看到她的脸,她的眼睛,湿漉漉的,像压着雨水,咩栗却在里面看见了另一个崭新的年纪,很干燥,可以尽情燃烧。
呜米似乎也怔了怔,缓慢地松开了手。咩栗手腕处的凉意消失了。
再见。她说。
高一的下半学期,咩栗再也没有见过呜米。
两人的重逢是七月末一场季风雨,五点钟的天蒙一层铅灰,咩栗站在书店门口的时候怀里抱着两本书,她抬头,仰望着世界像牢笼,皮肤潮湿,灵魂潮湿,听觉也跟着潮湿,呜米叫她的时候每个音节都像浸过水。她回头,看见刚跑进同一个屋檐下的呜米,短袖T恤,露出一截光滑的手臂,有水珠顺着滚下来。
咩栗感到不甘,她开始购买理科的教辅,同桌咬着酸奶吸管,看她的眼神活像见鬼。她问咩栗:你怎么了?咩栗瘪嘴,说我也想学理科。同桌倒吸一口气,说你疯了。
咩栗开始熬夜,终于在第三周的某个深夜被偏铝酸钠干趴。
她难受了一整晚,从第二天开始把物化生的教材全塞进抽屉最底下吃灰。
咩栗像一滚水,沸腾过后最终也冷下来。她看着呜米,总是突然觉得心脏溺水一阵子,挣扎着又醒过来呼吸了。她偶尔做梦,梦见一些呜米的碎片,比如最开始时她望过来的一眼,她的作业,她罩在自己身上的外衣...还有她们渐行渐远的未来。
但最后咩栗全都沉默着接受了。
高一时她仍然常常生病,生一些名字拗口念不干脆的病,她时常请假、坐在医院的候诊室里零零散散地读博尔赫斯的诗,然后领药回家,那些生僻字全都窸窸窣窣地混在一起,她也因此连味觉都曾败坏三分。可咩栗望着她的背影,嗓间默念着青绿色的年纪。
——十六、十六啊。唯一能和她仰望同一片天空的、蝴蝶般的十六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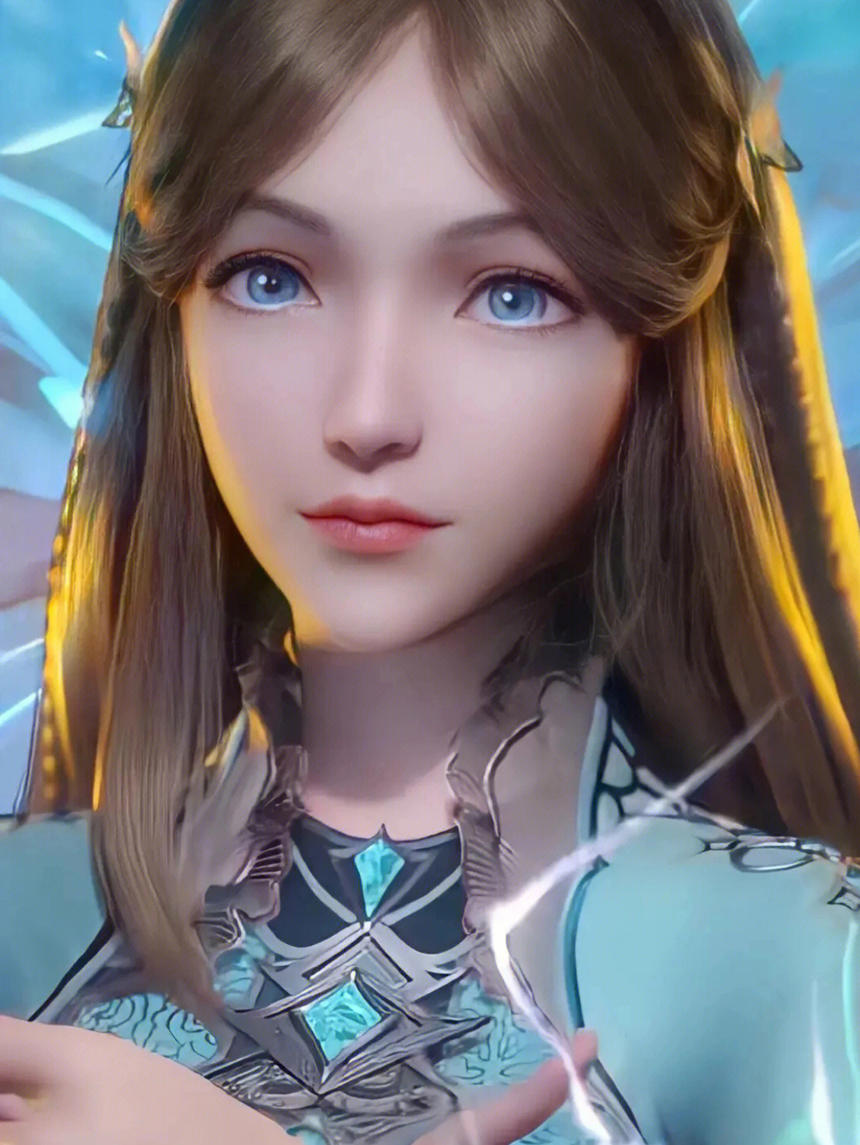
她闭上眼,仍觉得比糖甜。
分别的时候恰是流泪的天气,咩栗什么都不想地站着,十六骨的晴雨伞挂在她的手腕上。下午她还在这里听了最后一节地理课,晚修就已经没有她的位置了。她有些出神,只隐约记得自己被分去十七班,所幸还和同桌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团潮湿的空气,没有实质。呜米从外面跑进来,浑身淋得湿透,咩栗匆匆看了她一眼,以为这就是最后了。
而几秒后呜米拉住她的手腕,叫她。
咩栗。
咩栗略显错愕地看她,先是看到呜米手腕上的那根红绳,从袖筒里露出来,红色亮得扎眼,她再抬头看到她的脸,她的眼睛,湿漉漉的,像压着雨水,咩栗却在里面看见了另一个崭新的年纪,很干燥,可以尽情燃烧。
呜米似乎也怔了怔,缓慢地松开了手。咩栗手腕处的凉意消失了。
再见。她说。
高一的下半学期,咩栗再也没有见过呜米。
两人的重逢是七月末一场季风雨,五点钟的天蒙一层铅灰,咩栗站在书店门口的时候怀里抱着两本书,她抬头,仰望着世界像牢笼,皮肤潮湿,灵魂潮湿,听觉也跟着潮湿,呜米叫她的时候每个音节都像浸过水。她回头,看见刚跑进同一个屋檐下的呜米,短袖T恤,露出一截光滑的手臂,有水珠顺着滚下来。

 空与病娇璃月
空与病娇璃月















![[MeUmy]蜀月行歌](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61151_11471.jpg)
![[MeUmy]蜀月行歌](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517/165506_88481.jpg)
![[MeUmy]蜀月行歌](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1025/143808_25450.jpg)
![[MeUmy]蜀月行歌](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06/102954_54941.jpg)
![[MeUmy蜀月行歌二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永远不会消失](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43707_87579.jpg)
![[MeUmy蜀月行歌二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永远不会消失](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50417_892212.jpg)
![[MeUmy蜀月行歌二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永远不会消失](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50745_65793.jpg)
![[MeUmy蜀月行歌二创]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永远不会消失](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105/153752_63503.jpg)
![[Meumy]长安的月](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323/153007_71740.jpg)
![[Meumy]长安的月](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2/0517/180527_60956.jpg)
![[Meumy]长安的月](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202/142131_04900.jpg)
![[Meumy]长安的月](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220/102257_1213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