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志·白雪夫人》(2)(10)
秋熠仅剩的一只眼睛死死瞪着嬴无翳,而后仰天倒在了地上。
“若是在起初就有这样的打算,也算一个人物了,”嬴无翳点了点头。他手一抖,剑已经不在掌中。
身边的谢玄凝在拔剑的姿势上,愣愣的看着自己腰中的剑匣。他要拔剑救主,忽然发现剑已不在腰间。嬴无翳从他腰间拔剑还剑,他根本没有看清,更勿论秋熠落下,嬴无翳挥剑的一瞬。秋熠从最初就已经错了,和张博对阵,他其实更多一分逃生的机会。他不曾看见这位离侯是亲自提着斩马刀冲锋陷阵,一刀劈断了城门上的雪菊花大旗。
“还有人不要命的么?”张博恶狠狠的踏上一步看着剩下的男人们。
“张博,”嬴无翳低低的喝了一声。
张博只得收敛了杀心,不甘的退在一边。秋熠在他手中偷袭嬴无翳,对他无疑是耻辱。
嬴无翳负着手,扫了一眼俘虏们。周围静得如死,雷骑军操着马刀等待命令,俘虏们甚至不敢呼吸。他们的命都操在这个南蛮侯爵的手中,而从那双沉沉的眼中,他们根本看不出嬴无翳的想法。
嬴无翳转过身去:“杀!”
雷骑军的军士一起提刀上前。刀光比恐惧来得更快,俘虏们心头转过了“死”字,刀光已经落在了他们的头顶,而后他们剧烈的痛楚让他们不再有机会恐惧,只是本能的哀嚎。离军杀戮的手段凌厉而直接,或是直接砍断颈椎,或是一刀洞穿心口,对于老兵而言,无所谓让对手多受折磨,见惯了血的人,简单得就像宰杀猪羊。
刀落下去无论贵贱,都是一泼红血,溅在斑驳的墙壁上,显得更加肮脏。几个离军下手稍轻,重伤的俘虏狂嚎着脱着血迹往前爬去。纵然已经绝望,求生的本能还在,可是他们无处可去。或许是因为有些羞愧,不能一刀杀人的离军下手更凶,追上一步将伤者拖回来,一把抓住头发,将整个头颅剁了下来。
钦使面无血色,几乎晕厥过去。虽然已经准备除掉俘虏,可是亲眼看着这人如牲畜的屠场,他还是难以忍受。猛一抬头,嬴无翳那双沉沉的眼睛不带一点感情,正盯在他抽搐的脸上。钦使死死咬着牙,打了一个寒噤。
随从中的白毅漠然,按剑的手指微微颤了颤,扭头看向了屋外。
雷骑们以腕上的一片皮子擦去刀上的残血,纷纷收刀回鞘,屋子中骤然少了些人,视线开阔了。人的目光都落在张博的身上,他脚边正是那个裹着披风的女人,女人怀里还搂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仅剩们的两个俘虏都在张博旁边,雷骑们不敢抢在千夫长面前。
“张博!”谢玄低声道。
张博捏着马刀舔了舔嘴唇。不知怎么的,他有些犹豫,却不是还想着这个女人能被赏给自己。张博不愿多看她的眼睛和那张雪一样的脸,不过要下刀去杀这个女人,他又有些不忍。确实是个极美的女人,就像件名贵的瓷器,亲手去打碎,总是有些遗憾。
“若是在起初就有这样的打算,也算一个人物了,”嬴无翳点了点头。他手一抖,剑已经不在掌中。
身边的谢玄凝在拔剑的姿势上,愣愣的看着自己腰中的剑匣。他要拔剑救主,忽然发现剑已不在腰间。嬴无翳从他腰间拔剑还剑,他根本没有看清,更勿论秋熠落下,嬴无翳挥剑的一瞬。秋熠从最初就已经错了,和张博对阵,他其实更多一分逃生的机会。他不曾看见这位离侯是亲自提着斩马刀冲锋陷阵,一刀劈断了城门上的雪菊花大旗。
“还有人不要命的么?”张博恶狠狠的踏上一步看着剩下的男人们。
“张博,”嬴无翳低低的喝了一声。
张博只得收敛了杀心,不甘的退在一边。秋熠在他手中偷袭嬴无翳,对他无疑是耻辱。
嬴无翳负着手,扫了一眼俘虏们。周围静得如死,雷骑军操着马刀等待命令,俘虏们甚至不敢呼吸。他们的命都操在这个南蛮侯爵的手中,而从那双沉沉的眼中,他们根本看不出嬴无翳的想法。
嬴无翳转过身去:“杀!”
雷骑军的军士一起提刀上前。刀光比恐惧来得更快,俘虏们心头转过了“死”字,刀光已经落在了他们的头顶,而后他们剧烈的痛楚让他们不再有机会恐惧,只是本能的哀嚎。离军杀戮的手段凌厉而直接,或是直接砍断颈椎,或是一刀洞穿心口,对于老兵而言,无所谓让对手多受折磨,见惯了血的人,简单得就像宰杀猪羊。

刀落下去无论贵贱,都是一泼红血,溅在斑驳的墙壁上,显得更加肮脏。几个离军下手稍轻,重伤的俘虏狂嚎着脱着血迹往前爬去。纵然已经绝望,求生的本能还在,可是他们无处可去。或许是因为有些羞愧,不能一刀杀人的离军下手更凶,追上一步将伤者拖回来,一把抓住头发,将整个头颅剁了下来。
钦使面无血色,几乎晕厥过去。虽然已经准备除掉俘虏,可是亲眼看着这人如牲畜的屠场,他还是难以忍受。猛一抬头,嬴无翳那双沉沉的眼睛不带一点感情,正盯在他抽搐的脸上。钦使死死咬着牙,打了一个寒噤。
随从中的白毅漠然,按剑的手指微微颤了颤,扭头看向了屋外。
雷骑们以腕上的一片皮子擦去刀上的残血,纷纷收刀回鞘,屋子中骤然少了些人,视线开阔了。人的目光都落在张博的身上,他脚边正是那个裹着披风的女人,女人怀里还搂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仅剩们的两个俘虏都在张博旁边,雷骑们不敢抢在千夫长面前。
“张博!”谢玄低声道。
张博捏着马刀舔了舔嘴唇。不知怎么的,他有些犹豫,却不是还想着这个女人能被赏给自己。张博不愿多看她的眼睛和那张雪一样的脸,不过要下刀去杀这个女人,他又有些不忍。确实是个极美的女人,就像件名贵的瓷器,亲手去打碎,总是有些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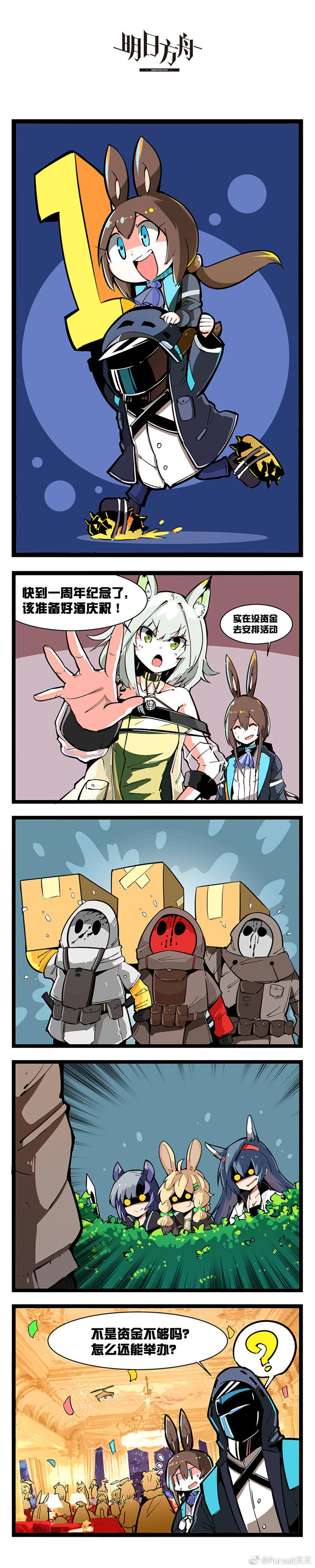
 tk第五人格红夫人
tk第五人格红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