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 5(5)(2)
2023-07-17 来源:百合文库
就好像这片玻璃构成的森林盆景中用预感来交换回忆的规则一样,我与他之间也遵从着用一人的存在来换取另一人的存在的规则。
由于我和他根本是平等的东西,这份规则用「将砝码在天平的两侧之间转移」这种说法更为合适。在他俯下身子将我拉起的同时,我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幻肢在触摸自己的灵魂。幻肢是由意识供养出的躯体,是依附于灵魂才能存在的可怜之物;它因从灵魂中抢夺养料而得以成活,于是我在能够无比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碰触的同时,也就明白了自己的灵魂是如此空乏和裸露。我任由他将我拉起,他身上的气息在这个时代只能在老电影中体味,而我嗅到的则比至今为止体味到的要强烈一万倍。即使是夏天也让人觉得要被冻住的海风,虽然自大洋而来还是在穿越草地和砖石楼的过程中沾染了更加丰富的气味。还有被熨烫过的羊毛制品和无意间洒在其上的咖啡。我安心地躺在了他的背上;这就是我灵魂的气味,令人舒适。原本还会以为自己的灵魂会更加呛鼻来着。
如今我不会去问接下来要去哪里,因为我意识到了至今为止的世界无论多么反常识,都对我们是如此亲切。天空如同木星表面的橙色褪去了,以浅灰色而代之,在夏日这意味着即将有降水到来,而我对此毫不担心。我们暂时躲藏的仓库被分解成了一块块的墙壁,天花板浮向半空,四面的墙壁不再竖直,以不同的角度漂浮起来。风扇从墙体上剥落,每一片扇叶、每一颗螺丝都解除了原有的连接,自由地漂浮在道路上方。与之对应,视野的远处有新的物体在被构成。想到缺乏变化的淡灰色的天空看起来与画布相仿,它的上方就出现了笔迹,是用很久没有削过的铅笔绘制的粗重线条,基本保持着平直的形态,但显然没有用尺子加以规范。三条左右的粗线条之后是无数细细短短的线,它们组成了数不清的三角形。这些三角形连接起来,一层,两层,三层,再被粘到粗线条上,压缩到一个薄薄的平面里。
它们从无关联的位置聚集起来,从散落在地的状态立起来,最终以一端贴合,显现出像是微缩版的埃菲尔铁塔那样的高压输电塔的形状。但我并不关心它是什么;接下来这些线条还会重新散开,这次不会再是原先的那些线条了。这座塔形的画面会不断再倾斜和再立直的过程,时而立体时而扁平,这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我的意义仅仅在于与同行的少年的某种奇妙的连接;只要我的灵魂还能供养出幻肢,我的意识又或许是他的意识就可以被他背在身后。
这样的话,就变得想要同他交谈了。如果现在去问他「你是谁」的话。
「我的名字叫S·格里默。」
原来这就是你的名字啊。
你可以帮助我想起自己的名字吗。
曾有一瞬觉得仿佛要想起自己的名字,终究还是远去了。如今的我只是在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愈发虚弱、愈发模糊。我观察着身边的景色,感觉到自己在河边。不久前似乎也曾路过河流,如今路过的河流与它并非同一条。这片水面相比之下宽阔得多,有鸣着汽笛的轮船来回移动,搅动着水面上橙色的光影。深紫色的水面上月光和灯光像是被摔碎在地上的玻璃球,不知为何叫人想要捡起,即使会让手指划伤。接着天空再度亮起,是因为月亮被轮船载着离去了。我再次看到了满天的朝霞,使我回想起木星的大气。少年自然是不可能在这片刻之间带我穿越地球两端的,因而我得以知晓我能见到这些景色无不是因为自己也正处于他的内部,如同他就在我的内部一样。可是这样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帮我回忆任何东西;他是我的载具,我的躯体,是我的感官的筛查官,但终究与我不同。这种违和感开始撕扯我与他的连接点,使我明白他并不是我。
由于我和他根本是平等的东西,这份规则用「将砝码在天平的两侧之间转移」这种说法更为合适。在他俯下身子将我拉起的同时,我明白了这是自己的幻肢在触摸自己的灵魂。幻肢是由意识供养出的躯体,是依附于灵魂才能存在的可怜之物;它因从灵魂中抢夺养料而得以成活,于是我在能够无比真切地感受到它的碰触的同时,也就明白了自己的灵魂是如此空乏和裸露。我任由他将我拉起,他身上的气息在这个时代只能在老电影中体味,而我嗅到的则比至今为止体味到的要强烈一万倍。即使是夏天也让人觉得要被冻住的海风,虽然自大洋而来还是在穿越草地和砖石楼的过程中沾染了更加丰富的气味。还有被熨烫过的羊毛制品和无意间洒在其上的咖啡。我安心地躺在了他的背上;这就是我灵魂的气味,令人舒适。原本还会以为自己的灵魂会更加呛鼻来着。
如今我不会去问接下来要去哪里,因为我意识到了至今为止的世界无论多么反常识,都对我们是如此亲切。天空如同木星表面的橙色褪去了,以浅灰色而代之,在夏日这意味着即将有降水到来,而我对此毫不担心。我们暂时躲藏的仓库被分解成了一块块的墙壁,天花板浮向半空,四面的墙壁不再竖直,以不同的角度漂浮起来。风扇从墙体上剥落,每一片扇叶、每一颗螺丝都解除了原有的连接,自由地漂浮在道路上方。与之对应,视野的远处有新的物体在被构成。想到缺乏变化的淡灰色的天空看起来与画布相仿,它的上方就出现了笔迹,是用很久没有削过的铅笔绘制的粗重线条,基本保持着平直的形态,但显然没有用尺子加以规范。三条左右的粗线条之后是无数细细短短的线,它们组成了数不清的三角形。这些三角形连接起来,一层,两层,三层,再被粘到粗线条上,压缩到一个薄薄的平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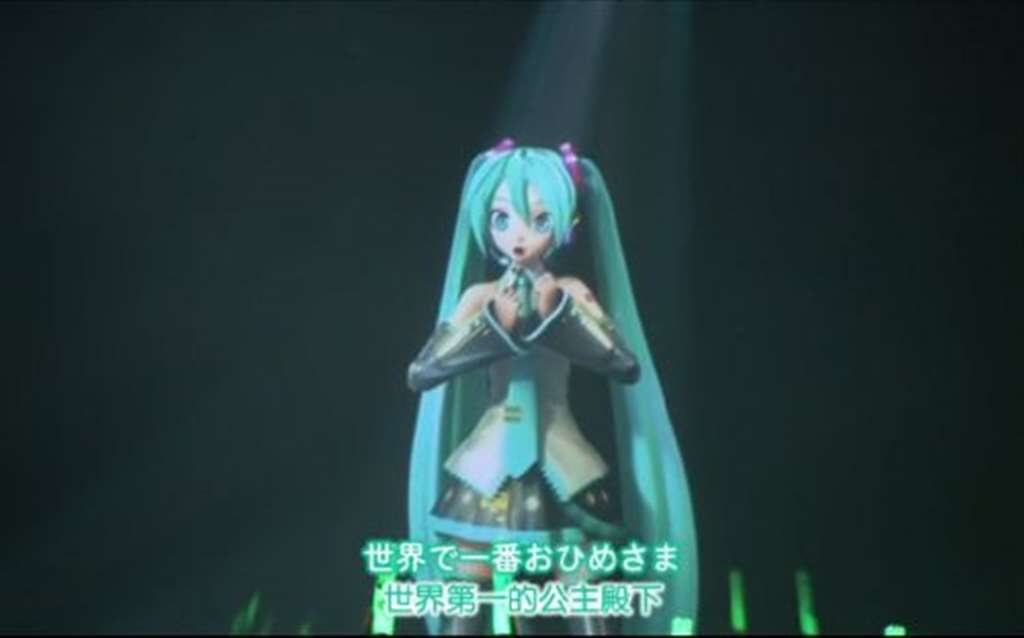
它们从无关联的位置聚集起来,从散落在地的状态立起来,最终以一端贴合,显现出像是微缩版的埃菲尔铁塔那样的高压输电塔的形状。但我并不关心它是什么;接下来这些线条还会重新散开,这次不会再是原先的那些线条了。这座塔形的画面会不断再倾斜和再立直的过程,时而立体时而扁平,这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我的意义仅仅在于与同行的少年的某种奇妙的连接;只要我的灵魂还能供养出幻肢,我的意识又或许是他的意识就可以被他背在身后。
这样的话,就变得想要同他交谈了。如果现在去问他「你是谁」的话。
「我的名字叫S·格里默。」
原来这就是你的名字啊。
你可以帮助我想起自己的名字吗。
曾有一瞬觉得仿佛要想起自己的名字,终究还是远去了。如今的我只是在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愈发虚弱、愈发模糊。我观察着身边的景色,感觉到自己在河边。不久前似乎也曾路过河流,如今路过的河流与它并非同一条。这片水面相比之下宽阔得多,有鸣着汽笛的轮船来回移动,搅动着水面上橙色的光影。深紫色的水面上月光和灯光像是被摔碎在地上的玻璃球,不知为何叫人想要捡起,即使会让手指划伤。接着天空再度亮起,是因为月亮被轮船载着离去了。我再次看到了满天的朝霞,使我回想起木星的大气。少年自然是不可能在这片刻之间带我穿越地球两端的,因而我得以知晓我能见到这些景色无不是因为自己也正处于他的内部,如同他就在我的内部一样。可是这样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帮我回忆任何东西;他是我的载具,我的躯体,是我的感官的筛查官,但终究与我不同。这种违和感开始撕扯我与他的连接点,使我明白他并不是我。
 all澄换命5
all澄换命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