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二部)(15)
“答应我一件事,好吗?不要去,算我求你了,不要去!”我不想睁开眼,一个人在床上拼命地呼喊着,眼睛里涌出了咸咸的泪水,它从我的脸颊下滑到我的嘴边,我抿了抿嘴,尝到了这股咸味,才微微地睁开了眼。
我走到了客厅,下意识地说了一声:“奶奶早上好。”我拿起了桌上蓝色书包,偶然瞥了一眼日历,才发现今天是假期,我坐在椅子上,渐渐地清醒了,霎时我明白奶奶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但我还在这个家中时,路过那个蛋糕店时,却仿佛能感受到她的存在,能听见她的唠叨。
我趴在冰凉的木桌上,看着昨晚吃剩的碗,知道自己还没有收拾,不过现在我也无心去收拾它们。我不断在记忆的海洋中寻找她的唠叨,我想我听过,只是我淡忘了。
我起身前往窗子那,似乎想起了另一个人,猛然懂得我在床上时所说的那个“你”是谁。
她是我的一位同学,准确来说我也该用“朋友”这个称谓。她不同于班上任何一位学生,她也是唯一一个追问过我上学迟到的原因的人,也因为这样,她成了最明白我的人,也许是因为她身为女性的感性,也许是因为我与她常常聊到我的内心上去。相对于那位“我最要好的朋友”,她给我带来得而非陪伴多,却对我来说有着一种强烈的归宿感。
她还是我的同桌,因此学习上我们经常互相帮助。我还记得一次英语课时,我小声地问她关于她的英文名字,她写出了歪歪扭扭的一个单词——“Judith”,我问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吗,她也只是点了点头。平时我很少见他说过几句话,更多的时候她会拿着家庭作业,指着上面的题,我懂她的意思,于是在草稿本上写下了过程,并附带我的讲解。
可是因为“强烈的归宿感”,我总是想避免和她有更多的交往,大多数都是在身为同学上的互帮互助,或许是我孤独得太久,这种感觉才会太过于强烈。我这样想,也不知是对她的不尊重。
一次放学后,那周内指定的组的人都要打扫卫生,由于我和她是同桌,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组里。他们很排挤我,在打扫里他们认为扫地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扫地并不是简单的活,但他们这样认为,恐怕一是因为这扫把不用洗,而这拖把还要洗,其次就是他们的惰性吧。拖地也要比倒垃圾这个位置好一点,因为倒垃圾需要上下楼,还要等他们扫完,等他们拖完。
如上,我只落得了一个“倒垃圾”的位置。
扫完地的人随便地放好扫把就互相有说有笑地走了,我坐在我的座位上,写着周末作业。拖完地的人随便洗洗拖把再随性地放到该放的地方后,也相互结伴地走了,我坐在我的座位上,收拾着书包。只剩下她留在教室里,她扫得很细心,一点也不像他们粗略地扫一遍,让地面沾沾水就算扫地。
我走到了客厅,下意识地说了一声:“奶奶早上好。”我拿起了桌上蓝色书包,偶然瞥了一眼日历,才发现今天是假期,我坐在椅子上,渐渐地清醒了,霎时我明白奶奶已经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但我还在这个家中时,路过那个蛋糕店时,却仿佛能感受到她的存在,能听见她的唠叨。
我趴在冰凉的木桌上,看着昨晚吃剩的碗,知道自己还没有收拾,不过现在我也无心去收拾它们。我不断在记忆的海洋中寻找她的唠叨,我想我听过,只是我淡忘了。
我起身前往窗子那,似乎想起了另一个人,猛然懂得我在床上时所说的那个“你”是谁。
她是我的一位同学,准确来说我也该用“朋友”这个称谓。她不同于班上任何一位学生,她也是唯一一个追问过我上学迟到的原因的人,也因为这样,她成了最明白我的人,也许是因为她身为女性的感性,也许是因为我与她常常聊到我的内心上去。相对于那位“我最要好的朋友”,她给我带来得而非陪伴多,却对我来说有着一种强烈的归宿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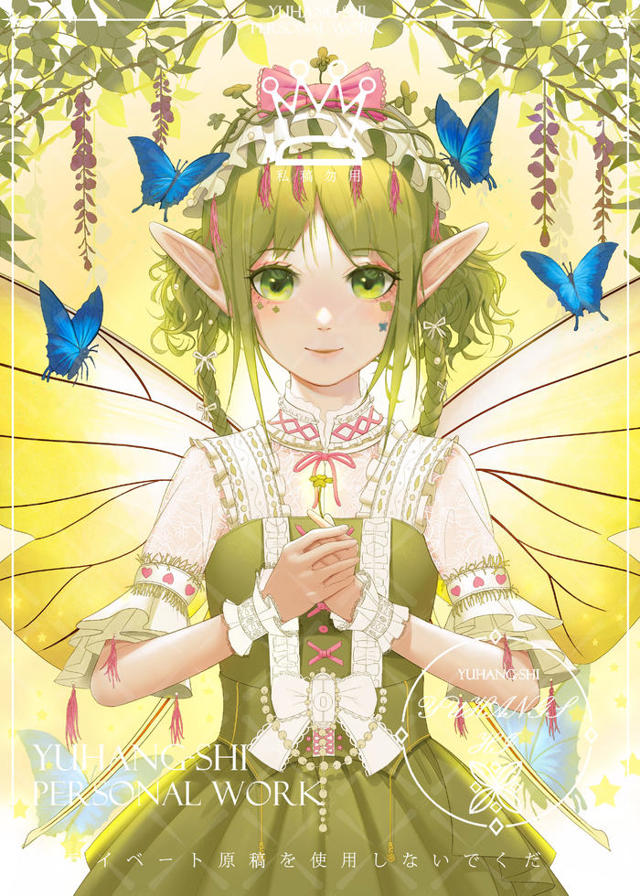
她还是我的同桌,因此学习上我们经常互相帮助。我还记得一次英语课时,我小声地问她关于她的英文名字,她写出了歪歪扭扭的一个单词——“Judith”,我问这是她的英文名字吗,她也只是点了点头。平时我很少见他说过几句话,更多的时候她会拿着家庭作业,指着上面的题,我懂她的意思,于是在草稿本上写下了过程,并附带我的讲解。
可是因为“强烈的归宿感”,我总是想避免和她有更多的交往,大多数都是在身为同学上的互帮互助,或许是我孤独得太久,这种感觉才会太过于强烈。我这样想,也不知是对她的不尊重。
一次放学后,那周内指定的组的人都要打扫卫生,由于我和她是同桌,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组里。他们很排挤我,在打扫里他们认为扫地是最简单的事情,其实扫地并不是简单的活,但他们这样认为,恐怕一是因为这扫把不用洗,而这拖把还要洗,其次就是他们的惰性吧。拖地也要比倒垃圾这个位置好一点,因为倒垃圾需要上下楼,还要等他们扫完,等他们拖完。
如上,我只落得了一个“倒垃圾”的位置。
扫完地的人随便地放好扫把就互相有说有笑地走了,我坐在我的座位上,写着周末作业。拖完地的人随便洗洗拖把再随性地放到该放的地方后,也相互结伴地走了,我坐在我的座位上,收拾着书包。只剩下她留在教室里,她扫得很细心,一点也不像他们粗略地扫一遍,让地面沾沾水就算扫地。

 旭凤和锦觅第二次双修
旭凤和锦觅第二次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