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与做事(8)
在人生头二十年接受各式各样教育的过程中,我就不止一次听老师和学长对我说:一个人首先是做人,其次才是做事,如果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他能成什么事?基于中国文化当中将人看得比事更重要的事实和现状,绝大多数精于世故的人在做学问之前,首先会跟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只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才能为他的钻研学问创造各种各样的便捷途径,倘若一个人跟周围所有人都闹僵了,那些看他不爽的人必定会对他群起而攻之,那么处境雪上加霜的他十有八九也只能丧失做学问的兴趣。
我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虽说乃是一个泱泱大国,智商高、潜力大的尖子生俯拾即是,但是古往今来却出不了几个世界级伟人的原因。一个大学问家最最首要的是做学问,一个人学术成就的高低决不依赖于他跟周围人关系相处得是否融洽,倘若一个人在做学问的同时还不得不抽出四五分的精力来兼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么分身乏术的他学问也很难深入下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985、211高校的教授学者智商都不低,但是能写出SCI的却屈指可数,按理说,写SCI并不难,但是既然在写论文的同时一个人必须分身不暇地应付周围复杂的人情网络,若要在一年之内发表出两三篇高质量的SCI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比登天还难。鲁迅先生曾多次提到过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我觉得将“人”凌驾在“事”之上并不能被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就是一个关系的社会,中国的“关系学”甚至体现在汉字当中,汉语不如英语那样,每一个词都有独立的词性和意义,理解一个汉字、一个词的意义必须依据其在句子中的地位、它跟前后词的关系,如果不顾它跟句中其他成分的联系将一个汉字或一个词撇出来单独考虑,那么我们只能断章取义地误读它的涵义,而西方哲学所信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认为现实的逻辑、规律和必然性必须首先要到语言中去找,就拿英语来说吧,每个词的词性在句子形成之前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比如xxx-ly必定是副词、xxx-ous、xxx-ive必定是形容词、 xxx-ness必定是名词、am、is、are肯定是联系前后短语之间的系词,换句话说,不管句子再怎么变,句子中每个词、每种成分的涵义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语言是如此,文化也必定是如此,在中国,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必定要放在他跟周围其他人的关系、他在环境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之下来考虑,讲句毫不客气的话,哪怕你将诺奖揽入怀中、哪怕你提出了惊世理论,只要你不把周围人哄开心了,所有人照样能把你臭得一文不值,甚至连一个老龙二都能指着鼻子数落你的不是,老牛吃嫩草的杨振宁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西方人呢?
你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哪怕所有人都看你不爽、人人都欲将你除之后快,也没有人能将你的成就跟你与周围人相处的和谐程度相提并论。
直到很多年以后,在现实的摸爬滚打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骨头的我才意识到处人的重要性,在当初我向爸爸宣战后搅得周围邻居不得安宁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对我抱有深深的成见:你中学毕业了就是应该考大学嘛!你零基础开始才弹几个月,考什么南艺钢琴系?哪有孩子跟父亲顶着干的,爸爸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在得罪了周围所有邻居、跟他们公开唱反调的情况下,我越是下狠心练琴,所有人就越反感我,他们甚至认为即便付出再大的努力,我在音乐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出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能读到“就你还弹钢琴呢”、“就你还考南艺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搞你的计算机吧”的刻板偏见,虽然早年那个不谙世事、固执死板的我总想着“用学术成就证明自己”、“在音乐上跟你一较高下”,并因而总是找不准解决人际纠纷的正确方法,但是当我意识到人际关系比做学术研究更重要、周围人会根据你跟他们关系的融洽与否来判断你学术能力的高低之后,我就开始想方设法地拉拢周围的人,投其所好甚至有事没事地给他们施一点小恩小惠,果不其然,没多久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拐弯,就连我们楼下本对我满腹怨言、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的S老师也开始在妈妈面前夸奖我:
我想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虽说乃是一个泱泱大国,智商高、潜力大的尖子生俯拾即是,但是古往今来却出不了几个世界级伟人的原因。一个大学问家最最首要的是做学问,一个人学术成就的高低决不依赖于他跟周围人关系相处得是否融洽,倘若一个人在做学问的同时还不得不抽出四五分的精力来兼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么分身乏术的他学问也很难深入下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985、211高校的教授学者智商都不低,但是能写出SCI的却屈指可数,按理说,写SCI并不难,但是既然在写论文的同时一个人必须分身不暇地应付周围复杂的人情网络,若要在一年之内发表出两三篇高质量的SCI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比登天还难。鲁迅先生曾多次提到过中国人的劣根性,但是我觉得将“人”凌驾在“事”之上并不能被归结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就是一个关系的社会,中国的“关系学”甚至体现在汉字当中,汉语不如英语那样,每一个词都有独立的词性和意义,理解一个汉字、一个词的意义必须依据其在句子中的地位、它跟前后词的关系,如果不顾它跟句中其他成分的联系将一个汉字或一个词撇出来单独考虑,那么我们只能断章取义地误读它的涵义,而西方哲学所信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则认为现实的逻辑、规律和必然性必须首先要到语言中去找,就拿英语来说吧,每个词的词性在句子形成之前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比如xxx-ly必定是副词、xxx-ous、xxx-ive必定是形容词、 xxx-ness必定是名词、am、is、are肯定是联系前后短语之间的系词,换句话说,不管句子再怎么变,句子中每个词、每种成分的涵义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语言是如此,文化也必定是如此,在中国,任何一个人的价值必定要放在他跟周围其他人的关系、他在环境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和角色之下来考虑,讲句毫不客气的话,哪怕你将诺奖揽入怀中、哪怕你提出了惊世理论,只要你不把周围人哄开心了,所有人照样能把你臭得一文不值,甚至连一个老龙二都能指着鼻子数落你的不是,老牛吃嫩草的杨振宁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西方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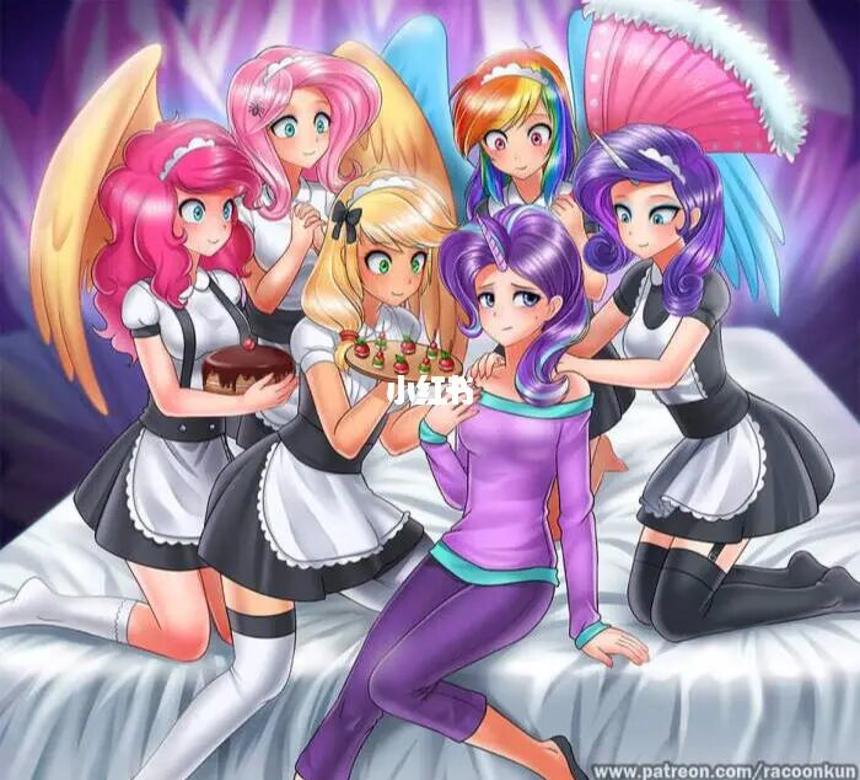
你什么水平就是什么水平,哪怕所有人都看你不爽、人人都欲将你除之后快,也没有人能将你的成就跟你与周围人相处的和谐程度相提并论。
直到很多年以后,在现实的摸爬滚打中被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完整骨头的我才意识到处人的重要性,在当初我向爸爸宣战后搅得周围邻居不得安宁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对我抱有深深的成见:你中学毕业了就是应该考大学嘛!你零基础开始才弹几个月,考什么南艺钢琴系?哪有孩子跟父亲顶着干的,爸爸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在得罪了周围所有邻居、跟他们公开唱反调的情况下,我越是下狠心练琴,所有人就越反感我,他们甚至认为即便付出再大的努力,我在音乐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出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能读到“就你还弹钢琴呢”、“就你还考南艺呢”、“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搞你的计算机吧”的刻板偏见,虽然早年那个不谙世事、固执死板的我总想着“用学术成就证明自己”、“在音乐上跟你一较高下”,并因而总是找不准解决人际纠纷的正确方法,但是当我意识到人际关系比做学术研究更重要、周围人会根据你跟他们关系的融洽与否来判断你学术能力的高低之后,我就开始想方设法地拉拢周围的人,投其所好甚至有事没事地给他们施一点小恩小惠,果不其然,没多久他们对我的态度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拐弯,就连我们楼下本对我满腹怨言、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的S老师也开始在妈妈面前夸奖我:
 动物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动物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