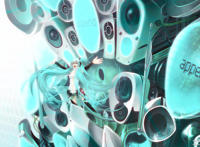帝皇军团——王座守望者第二章(2)
我有时候在想,这些知识是我们众多的负担中最沉重的一种。任何心怀目标的人都会困兽犹斗。我们止不住地去想,我们已把最初为之战斗的目标抛在身后,却向一个幻灭的虚影献上忠诚。
但我们依旧在保护,倾心于那些幸存下来的珍贵之物,我们寻求在任何事物上体现祂的意志,当黑暗聚集之时,我们坚守祂的光芒,我们解释、我们研究、我们钻研那些旧日的哲学。
我们有许多职责,而这本该如此,因为我们并非形单影只的创造物,千万年的时间在很多方面改造了我们,但我们的职责不变。
我们千人千面,但我们绝不只是战士。
我叫瓦雷利安,禁军巴列奥略大厅的盾卫连长(shield-Captain of the palaiologain chamber of the Hykanatoi)如同我所有的兄弟们一样,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它们被一个接着一个地镌刻在我的胸甲内部。有些名字通过战斗获得,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对神秘事物的沉思。我们坚持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虽然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正确地遵从了沉思这项仪式本身。这场绵延千年的倒退已经让太多的东西被遗忘,所以现在对于一切来说最重要的便是确信了。
在我们的神学体系里,我们谈论着眀了之识(speculum certus)和未明之识(speculum obscurus)。前者研究的是已知的东西,若这让你觉得是毫无意义的,请容许我反驳。因为知道帝皇在说什么是一回事,但明白祂的言语中蕴含着什么意思就是另一回事了。
祂没有留下手写的记录。一切我们对祂的了解都来自于一些记录者的追忆,或是拜虔信所赐的美好景象。因此,当一件事出现在含义明确的圣典里时,其背后蕴含的含义依旧难窥堂奥。在祂坐上黄金王座一百年后,祂被记录在羊皮纸的言语就难以解读,众人为解释清楚就争论了一万年。服务于霸权之塔中的学者,一生都致力于解释这些话语碎片中的内容,我们从不会蔑视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的研究是为了掀开命运的面纱。即使是现在,我们仍能通过对当时那些学者的话语的冥想获得启迪。
但如果对确信之识我们都尚存争议,那对晦涩之识的争论则毫无用处,因为帝皇留下了太多未经阐述之物,而我们相信迟早祂会把这些解释清楚。有些东西祂希望我们能知晓,但现在只能将其记录下来。自霸权之塔树立以来,我们在这座塔上注视着全人类的领域,我们仅能推测这是祂的意图。这即是对皇帝意志的研究,只能从梦境和对神秘而晦涩逻辑的耐心研究中将其显现。
但我们依旧在保护,倾心于那些幸存下来的珍贵之物,我们寻求在任何事物上体现祂的意志,当黑暗聚集之时,我们坚守祂的光芒,我们解释、我们研究、我们钻研那些旧日的哲学。
我们有许多职责,而这本该如此,因为我们并非形单影只的创造物,千万年的时间在很多方面改造了我们,但我们的职责不变。
我们千人千面,但我们绝不只是战士。
我叫瓦雷利安,禁军巴列奥略大厅的盾卫连长(shield-Captain of the palaiologain chamber of the Hykanatoi)如同我所有的兄弟们一样,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名字,它们被一个接着一个地镌刻在我的胸甲内部。有些名字通过战斗获得,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于对神秘事物的沉思。我们坚持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虽然我不确定我们是否正确地遵从了沉思这项仪式本身。这场绵延千年的倒退已经让太多的东西被遗忘,所以现在对于一切来说最重要的便是确信了。

在我们的神学体系里,我们谈论着眀了之识(speculum certus)和未明之识(speculum obscurus)。前者研究的是已知的东西,若这让你觉得是毫无意义的,请容许我反驳。因为知道帝皇在说什么是一回事,但明白祂的言语中蕴含着什么意思就是另一回事了。
祂没有留下手写的记录。一切我们对祂的了解都来自于一些记录者的追忆,或是拜虔信所赐的美好景象。因此,当一件事出现在含义明确的圣典里时,其背后蕴含的含义依旧难窥堂奥。在祂坐上黄金王座一百年后,祂被记录在羊皮纸的言语就难以解读,众人为解释清楚就争论了一万年。服务于霸权之塔中的学者,一生都致力于解释这些话语碎片中的内容,我们从不会蔑视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的研究是为了掀开命运的面纱。即使是现在,我们仍能通过对当时那些学者的话语的冥想获得启迪。
但如果对确信之识我们都尚存争议,那对晦涩之识的争论则毫无用处,因为帝皇留下了太多未经阐述之物,而我们相信迟早祂会把这些解释清楚。有些东西祂希望我们能知晓,但现在只能将其记录下来。自霸权之塔树立以来,我们在这座塔上注视着全人类的领域,我们仅能推测这是祂的意图。这即是对皇帝意志的研究,只能从梦境和对神秘而晦涩逻辑的耐心研究中将其显现。

 霍雨浩把冰雪二帝c
霍雨浩把冰雪二帝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