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 古风 凌肖(二)(3)
对方一愣,没想到你竟然还记挂他的伤势,有什么东西似乎融化了,在胸口汇聚成溪流,渐渐蔓延全身,他眯了眯眼,手指扣在你脑门,笑意盈然地回道:“既然你这么关心我,那待会儿你帮我换药吧,如何,娘子?”
他语调淡淡的,却不轻不重地咬了“娘子”这两个字,眼看着你耳朵泛上红霞,唇角弧度加深。
“蛤?”你捂着脑袋,气鼓鼓地瞪他,对方早就摘了斗笠,整个人笼在细如蝉翼的晨光中,宛如玉树迎风而立。奇异发色在金芒下折射出别样的炫彩,愈加衬得他面容清朗,眉宇间的锐气也尽数敛去,只余一抹戏谑之色。
假如说那晚的他像玉面修罗,那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浪荡的金玉纨绔,还是那种特别愿意占你便宜的那种。
“谁是你娘子?才不管你!”你又羞又恼,把怀里东西一股脑塞给他,临了还附赠一记白眼,掉头往回走。
没两步,就听见后面东西骨碌碌滚落,随后是一声闷哼,回头看去,男子颓然瘫坐在地,脸色煞白。
你大惊失色,忙冲上去扶起他,对方却仍是满不在乎的口气,半垂着眼,读不出任何情绪:“你不是说不管我么,让我疼死算了!”
你气急败坏地吼他,“说什么胡话!”他一愣,乖乖认怂。
你把他扛进房内靠在床沿,替他褪去外衣,白色绷带已经被鲜血浸透,变成暗红色,你轻手轻脚地拆开,一点点重新上药。全然没注意到他灼灼的视线,一瞬未曾偏离地注视着你。
几缕青丝划过他裸露在外的胸膛,冰冰凉凉的,他眼中光影颤动,手指不自觉绕进其中,随意把玩着。
等一切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你才猛然意识到刚刚做了什么,竟然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替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宽衣解带,还直接看光光!你脸刷地红透大半,同手同脚地走到桌边,故作镇定地给自己倒水喝,手却抖得厉害,差点把茶壶打翻。
对方狐疑地目送你走远,拈起衣带,不满地问你:“喂,就这么走了?扒光了就不管了?我就这么衣衫不整地出去???”
他语调淡淡的,却不轻不重地咬了“娘子”这两个字,眼看着你耳朵泛上红霞,唇角弧度加深。
“蛤?”你捂着脑袋,气鼓鼓地瞪他,对方早就摘了斗笠,整个人笼在细如蝉翼的晨光中,宛如玉树迎风而立。奇异发色在金芒下折射出别样的炫彩,愈加衬得他面容清朗,眉宇间的锐气也尽数敛去,只余一抹戏谑之色。
假如说那晚的他像玉面修罗,那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浪荡的金玉纨绔,还是那种特别愿意占你便宜的那种。
“谁是你娘子?才不管你!”你又羞又恼,把怀里东西一股脑塞给他,临了还附赠一记白眼,掉头往回走。
没两步,就听见后面东西骨碌碌滚落,随后是一声闷哼,回头看去,男子颓然瘫坐在地,脸色煞白。

你大惊失色,忙冲上去扶起他,对方却仍是满不在乎的口气,半垂着眼,读不出任何情绪:“你不是说不管我么,让我疼死算了!”
你气急败坏地吼他,“说什么胡话!”他一愣,乖乖认怂。
你把他扛进房内靠在床沿,替他褪去外衣,白色绷带已经被鲜血浸透,变成暗红色,你轻手轻脚地拆开,一点点重新上药。全然没注意到他灼灼的视线,一瞬未曾偏离地注视着你。
几缕青丝划过他裸露在外的胸膛,冰冰凉凉的,他眼中光影颤动,手指不自觉绕进其中,随意把玩着。
等一切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你才猛然意识到刚刚做了什么,竟然在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替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男人宽衣解带,还直接看光光!你脸刷地红透大半,同手同脚地走到桌边,故作镇定地给自己倒水喝,手却抖得厉害,差点把茶壶打翻。
对方狐疑地目送你走远,拈起衣带,不满地问你:“喂,就这么走了?扒光了就不管了?我就这么衣衫不整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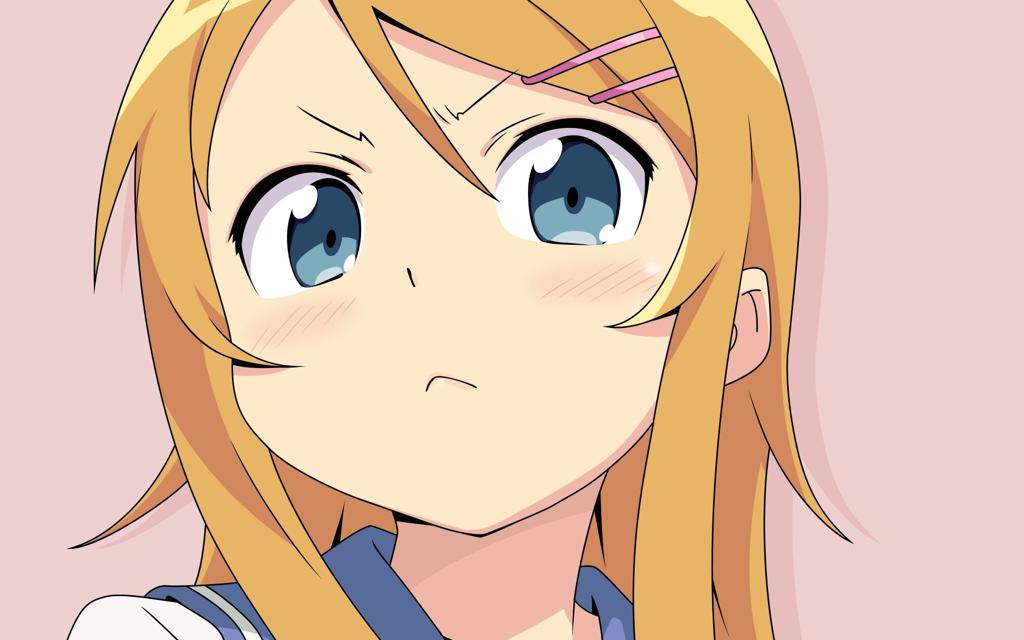
 旧巷笙歌板子古风
旧巷笙歌板子古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