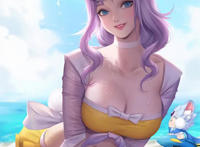山河复兴/(2)
这孙zei是真不睡觉吧。
——欸今儿不成,缺心眼儿有工作,等我们回来补上啊!
后面隐约还有九龙催促他的声音,杨九郎轻笑,做什么梦的,过了这村没这店。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回的。
大概能想到张九龄骂街的样子,嗯,爽。
解决了早饭,他慢吞吞把盘子拿去水槽里洗了,早知道这么麻烦,就不用盘子了,本想着稍微精致点,谁知道自找麻烦。
上午还能干什么呢?杨九郎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果然,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忙的时候嫌累,空的时候嫌空虚。
在家不知道折腾些什么,被张云雷的一通电话拉出门。
七月中的北京已经很热,九十点钟更是,一脚跨出单元门,他已经察觉后背出了层汗。
怕人认出来,压着帽檐往下,更是要不得。
更加缺心眼儿的,无非是杨九郎的车是黑的,吸热过快,一拉开车门,活活进了火炉似的,迫不得已又在车门口等了好久。
热的都快蒸发了,他又特别容易出汗,短短五分钟,背后已经黏了一层汗。
张云雷要是没什么大事儿喊他,害得他出那么多汗,全身不好受,他...
说起来,他也不能做什么。
张云雷从玫瑰园搬出来,也有一年了,工作越来越多,加上玫瑰园远,交通不便,他就算心里不乐意和先生分开,还是老老实实搬家。
房子是杨九郎给找的,重新刷漆装修,方便他拎包入住。
搬家第一天,他竟真有些从娘家被赶出来的小媳妇模样,亏得九郎熟悉这人脾气,厚着脸皮又是腻咕人,又是哄,才好一些。
备用钥匙九郎这里还有一把,不为别的,有时候急着找点东西,也方便。
他不去纠结这把钥匙是不是有别的含义,也不随意去猜测角儿的意思,人说句什么,他照做。
张云雷搬进屋的第一天,杨九郎便把装修师傅那里的几把钥匙,加上自己手头的一把,全给了他。
统共五把钥匙,他就收了四把。
“你拿着一把吧,我忘性大。”
他讲这话时,可是连头都不抬一下,弄得九郎以为,这小祖宗还没缓过来,还得哄着。
应了一声就把钥匙收进了口袋里,事后和自己的家门钥匙挂在一起。
这样他忘了,自己也不至于忘记。
张云雷话不肯多说,台下和舞台上差别确实很大。
内部被说成是重生历劫之后,才越发明显。
大抵命都是抢来的,他成熟稳重,自信谦虚。真情实感面对着观众,倒不负外界所说的老艺术家的称呼。
杨九郎已经很少见过台下的角儿有多爱撒娇,似乎台上如何撒娇耍痴,可下了台,换张脸,他还是极稳重。
那天上先生家,他坐着朝先生撒娇,露出一个与安迪差不多的笑,杨九郎远远的站着,才隐约真切的感觉到,这人,还是个孩子。
他实在讲不出张云雷对他于旁人是否有不一样的,但无论是不是的,很多东西未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欸今儿不成,缺心眼儿有工作,等我们回来补上啊!
后面隐约还有九龙催促他的声音,杨九郎轻笑,做什么梦的,过了这村没这店。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回的。
大概能想到张九龄骂街的样子,嗯,爽。
解决了早饭,他慢吞吞把盘子拿去水槽里洗了,早知道这么麻烦,就不用盘子了,本想着稍微精致点,谁知道自找麻烦。
上午还能干什么呢?杨九郎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果然,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忙的时候嫌累,空的时候嫌空虚。
在家不知道折腾些什么,被张云雷的一通电话拉出门。
七月中的北京已经很热,九十点钟更是,一脚跨出单元门,他已经察觉后背出了层汗。
怕人认出来,压着帽檐往下,更是要不得。
更加缺心眼儿的,无非是杨九郎的车是黑的,吸热过快,一拉开车门,活活进了火炉似的,迫不得已又在车门口等了好久。
热的都快蒸发了,他又特别容易出汗,短短五分钟,背后已经黏了一层汗。
张云雷要是没什么大事儿喊他,害得他出那么多汗,全身不好受,他...
说起来,他也不能做什么。
张云雷从玫瑰园搬出来,也有一年了,工作越来越多,加上玫瑰园远,交通不便,他就算心里不乐意和先生分开,还是老老实实搬家。
房子是杨九郎给找的,重新刷漆装修,方便他拎包入住。
搬家第一天,他竟真有些从娘家被赶出来的小媳妇模样,亏得九郎熟悉这人脾气,厚着脸皮又是腻咕人,又是哄,才好一些。
备用钥匙九郎这里还有一把,不为别的,有时候急着找点东西,也方便。
他不去纠结这把钥匙是不是有别的含义,也不随意去猜测角儿的意思,人说句什么,他照做。
张云雷搬进屋的第一天,杨九郎便把装修师傅那里的几把钥匙,加上自己手头的一把,全给了他。
统共五把钥匙,他就收了四把。
“你拿着一把吧,我忘性大。”
他讲这话时,可是连头都不抬一下,弄得九郎以为,这小祖宗还没缓过来,还得哄着。
应了一声就把钥匙收进了口袋里,事后和自己的家门钥匙挂在一起。
这样他忘了,自己也不至于忘记。
张云雷话不肯多说,台下和舞台上差别确实很大。
内部被说成是重生历劫之后,才越发明显。
大抵命都是抢来的,他成熟稳重,自信谦虚。真情实感面对着观众,倒不负外界所说的老艺术家的称呼。
杨九郎已经很少见过台下的角儿有多爱撒娇,似乎台上如何撒娇耍痴,可下了台,换张脸,他还是极稳重。
那天上先生家,他坐着朝先生撒娇,露出一个与安迪差不多的笑,杨九郎远远的站着,才隐约真切的感觉到,这人,还是个孩子。
他实在讲不出张云雷对他于旁人是否有不一样的,但无论是不是的,很多东西未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山河令车
山河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