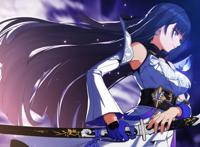灼灼其华(二)
二、
闹钟的尖叫声将我从床的封印中捞起来,我顶着乱蓬蓬的头发,挣扎着撬开牢牢闭合的眼睛,一把拍上闹钟,它终于委屈巴巴地缄了声。
长长叹了口气,只得一步三回头地挪进浴室,洗漱梳头,更衣化妆,新的一天总是这样匆匆忙忙地拉开帷幕,赶地铁,顺便买上一份早餐,到校,打卡,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资料,补论文,到了时间飞一样地赶去学院上课,待从学院那像教堂一样宏大的教室挪出来透口气时,已经夕阳西下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有这时我才能稍稍来首诗平缓一下陀螺一般的一天,为自己连轴转的生活来点诗意。
我叫柳容悦,上个月刚过了十九岁生日,是一名在读大三学生,我堪称普通的过分,普通的长相,还因为架了副眼镜显得极像个书呆子,普通的身高,还没有特别出众的身材,唯一能显摆一下的可能就是一头乌黑发亮像校园剧女主一样回头率颇高的瀑布长发,却还因为成天地埋在学业论文里而乱糟糟的,以至于只能扎个又黑又粗的马尾辫,这样一来,我就又只是个芸芸众生的有机分子了。
再说身世背景,这方面我就更可以用“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了,我就没见过我爸爸,听妈妈以前说,是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离了婚,于是我打心眼里痛恨这世上的男人,女人又要生孩子还要哄老公,还要忙工作当白领,当个女人那么辛苦,男人还要挑三拣四,不过我大可不必这么愤愤不平,因为我实在太过平凡,平凡到19年了也没一个男生追过我。
而和我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在去年因为肺癌晚期匆匆离开,从确诊到母亲永远离开我,不过半年不到,这让我实在痛苦不已,那段时间日日如行尸走肉一般游离,以泪洗面,就好像把我这辈子没流过的眼泪都流干了一样,生不如死。
好在没什么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一年过去,我已能从悲痛欲绝中堪堪走出,以忙碌到四脚朝天的生活来填补内心巨大的创伤。
只是,每到夜阑人静时,我总会借着床头灯昏黄却暖意融融的光芒,插上耳机,把自己沉浸静谧而又从容的乐声中,这是独属于我的单人世界,那里有一个在我心底扎了根再也挥之不去的名字——
张国荣。
十六年了,我从没对旁人说过那个我与他奇异的初见,因为我知道,十六年的浮浮沉沉,却将他早已消逝的身影勾勒地越发清晰,他成了太多人心头的一根刺,是太多人心底柔软的一片空地,所以即使我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那个三岁的小孩,会在这个巨星最后一天最后的时光里,留下她欢快的笑声和稚嫩的童音。
但我没法停止对他的想念,那道永恒的伤疤就那样横在心里,一经回忆,便是带着血腥的甜蜜。
《风继续吹》还在柔柔地唱着,我合上眼,脑里不自觉地浮现出十六年前的画面,已不甚清楚,却在极力回想中被迫清晰——
一个小女孩站在马路边,而蹲在她身边虚抱着她的是一个俊朗的男子,他笑得甚是动人。
我自认为在回忆中慢慢入睡了。
睁眼,我在一瞬间大脑短路,惊的话都说不出来。
 GV创造营writeas二
GV创造营writeas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