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预定的结局
在很久很久以前,但是没有人清楚那到底是是多久之前,久得甚至连时间都已经不记得了。那时的大地上有着一片的祥和与广阔宁静,青松翠柏,绿杨青柳,小溪河畔,雀啼蝉鸣,真似一副五彩玉石雕刻的场景;高峰白云翻滚,山谷云雾缭绕。
只可惜这一切没有延续很久。
在这片远土大地之上,有大大小小的城堡,里面住着富足的一家人;也有几座势均力敌的城池,长年以来都试图吞噬对方,多年的刀兵相见,已然是不共戴天,因死伤太多而不得不达成了停战协议,并每年送去一匹士兵到西北边的山谷。广阔的田野无边无际,风吹麦田起伏好似金色海洋里的波浪,一片只要被风吹动就会翻滚的金子。人们住着石头和泥土堆砌的房子,屋顶架着木头盖着茅草,圈养着一些牲畜,吃着田里农耕的美味蔬菜,生活不算富足,但衣食无忧。
一个秋天的清晨,阳光洒在还没有叶落的树梢上,村里的人们在鸡鸣过后陆陆续续走出了自家的门,有扛着锄头上地里干活的,有小孩出来割草喂羊的,一位妇人挎着堆满衣服竹篮,正不紧不慢地踏着轻快的步子在铺着零散石子的小路上走着。天气渐凉,她围上了头巾。
这条路直通流过村边的小河,这条河和村里的井养活着这个村子世世代代的人。河水不是很清澈,但足以看清河床的淤泥和石头。河水很浅,阳光通入河底,偶尔还可以看到河里的闪光来回晃动,那是游来游去的几条鱼,可能正在讨论着最近发生的不寻常的事。
妇人来到河边,望着清晨波光粼粼的河面,放下竹篮准备洗衣服。她用手在河里来回划了几下,河水还是很凉,妇人略微犹豫了一会,便挽起自己的袖管,在河边忙活着。
太阳升高了一点,离开了山头,可是原本早该吵吵闹闹的鸟儿们,到现在还是无声无息,仅偶尔可以看到它们匆匆飞过的身影。妇人没有在意这些,只是略微看了看四周,只见风吹着枯黄的野草左摇右摆,她就又埋头继续洗衣服。
洗着洗着,妇人微微皱眉,长吁了一口气,看着本该洗净的衣服怎么越洗越脏。妇人觉得不对劲,看看河里的水好像也没刚才那样干净了,但是自己的衣服也没脏到足以让河水浑浊成那般样子的啊。
正定神想着,妇人看到有大片的黑水漂了过来。一丝一丝,一点一点,一条一条,黑色污染着片片河水,小鱼儿四散逃开,好像被捕食者追捕者一样远离了黑色的恶水。
妇人把衣服放在了青石上,她有些慌乱,没注意衣服的一角还泡在河水中,便抬头望着恶水漂来的方向。河边有一颗大树,它的叶子还是绿油油的,树荫盖过了水面可以遮到河的对岸,河面上伸出一条粗壮的树根便是它其中的一条,长年的浸泡使树根上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周围也长着一些杂草。妇人仔细一看,发现上面还卡着一个脏乎乎的东西,看起来感觉还圆滚滚的,脏水的源头就是从那上面发出来的。
这是谁家的猪死了?妇人疑惑的站起身,把湿漉漉的手甩了甩,转头看看四周,没什么人,只有身边空旷的草丛,还有河对岸深幽的树林。
转头看向那个脏东西,妇人甩去手上的水并在衣服上蹭了蹭,提着裙腿,高抬脚跨过草丛,顺便在大树旁捡起一根长长的木棍,准备把碍事的脏东西捅出去,顺着水流就会漂到下游了。
只可惜这一切没有延续很久。
在这片远土大地之上,有大大小小的城堡,里面住着富足的一家人;也有几座势均力敌的城池,长年以来都试图吞噬对方,多年的刀兵相见,已然是不共戴天,因死伤太多而不得不达成了停战协议,并每年送去一匹士兵到西北边的山谷。广阔的田野无边无际,风吹麦田起伏好似金色海洋里的波浪,一片只要被风吹动就会翻滚的金子。人们住着石头和泥土堆砌的房子,屋顶架着木头盖着茅草,圈养着一些牲畜,吃着田里农耕的美味蔬菜,生活不算富足,但衣食无忧。
一个秋天的清晨,阳光洒在还没有叶落的树梢上,村里的人们在鸡鸣过后陆陆续续走出了自家的门,有扛着锄头上地里干活的,有小孩出来割草喂羊的,一位妇人挎着堆满衣服竹篮,正不紧不慢地踏着轻快的步子在铺着零散石子的小路上走着。天气渐凉,她围上了头巾。
这条路直通流过村边的小河,这条河和村里的井养活着这个村子世世代代的人。河水不是很清澈,但足以看清河床的淤泥和石头。河水很浅,阳光通入河底,偶尔还可以看到河里的闪光来回晃动,那是游来游去的几条鱼,可能正在讨论着最近发生的不寻常的事。
妇人来到河边,望着清晨波光粼粼的河面,放下竹篮准备洗衣服。她用手在河里来回划了几下,河水还是很凉,妇人略微犹豫了一会,便挽起自己的袖管,在河边忙活着。
太阳升高了一点,离开了山头,可是原本早该吵吵闹闹的鸟儿们,到现在还是无声无息,仅偶尔可以看到它们匆匆飞过的身影。妇人没有在意这些,只是略微看了看四周,只见风吹着枯黄的野草左摇右摆,她就又埋头继续洗衣服。
洗着洗着,妇人微微皱眉,长吁了一口气,看着本该洗净的衣服怎么越洗越脏。妇人觉得不对劲,看看河里的水好像也没刚才那样干净了,但是自己的衣服也没脏到足以让河水浑浊成那般样子的啊。
正定神想着,妇人看到有大片的黑水漂了过来。一丝一丝,一点一点,一条一条,黑色污染着片片河水,小鱼儿四散逃开,好像被捕食者追捕者一样远离了黑色的恶水。
妇人把衣服放在了青石上,她有些慌乱,没注意衣服的一角还泡在河水中,便抬头望着恶水漂来的方向。河边有一颗大树,它的叶子还是绿油油的,树荫盖过了水面可以遮到河的对岸,河面上伸出一条粗壮的树根便是它其中的一条,长年的浸泡使树根上长满了绿色的青苔,周围也长着一些杂草。妇人仔细一看,发现上面还卡着一个脏乎乎的东西,看起来感觉还圆滚滚的,脏水的源头就是从那上面发出来的。
这是谁家的猪死了?妇人疑惑的站起身,把湿漉漉的手甩了甩,转头看看四周,没什么人,只有身边空旷的草丛,还有河对岸深幽的树林。
转头看向那个脏东西,妇人甩去手上的水并在衣服上蹭了蹭,提着裙腿,高抬脚跨过草丛,顺便在大树旁捡起一根长长的木棍,准备把碍事的脏东西捅出去,顺着水流就会漂到下游了。
 崩坏三符华最后结局
崩坏三符华最后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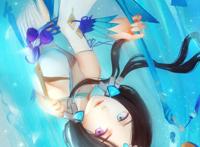

![Circle A结局完结碎碎念 || 阶段总结/B结局预告|[华晨宇水仙文]飒卷/卷炸](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17/104908_02322.jpg)
![Circle A结局完结碎碎念 || 阶段总结/B结局预告|[华晨宇水仙文]飒卷/卷炸](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424/135437_61009.jpg)
![Circle A结局完结碎碎念 || 阶段总结/B结局预告|[华晨宇水仙文]飒卷/卷炸](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529/153151_1249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