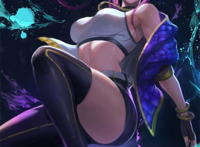大风
起风了,莫名的想起了她,她,近日过的还好吗?
微风抚过她的眉梢,却吹不开她紧锁的眉头,也吹不散那愁绪。
她总是为一些她认为应该伤感的事物而伤感着,我也曾劝慰过她,美好背后的寂寥,与万象更新的代价,我已经在很小心的措辞了,却还是敌不过美人一枝梨花带雨的泪。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她的心中,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我们却都是带着罪恶在这世间活着。
春天消融的残雪,夏日干涸的河塘,秋天凋零的落叶,冬日冻死归鸟……如此这些,都成为了一把悬挂在她眉头上的铁锁,锁住了朱颜。
我很少见她笑过,黛眉轻蹙,似是她的常态。
我常笑话她是一个矫情的人,但正是因为这种矫情,才将她与那些庸脂俗粉分隔开来,在我的心中, 她是不同,也是唯一。
我想,我是喜欢上她了。
想起了那串她吃剩下的冰糖葫芦,银牙轻咬,我看得见她眼中闪过的欣喜,却是坚持不肯再吃一口,咽着口水,倔强的将头偏向一边。这样子的她,真的很可爱。
“这是什么?”她问我说。
“你没吃过吗?这叫做冰糖葫芦,一种很美味的小吃。”
“没有~”她咬下一颗,很诚实的点了点头。
她笑的很甜,就像是包裹在山楂上的糖衣,却是转瞬即逝。
“你怎么不吃了?”看着她忽然冷下来的笑颜,没由来的,我忽然赶到有些不安。
“你说,我这样咬它一口, 它真的不会感到疼吗?”话音未落,拴着珍珠的弦就已经断了。
低下头,我正好看到她手背上那个还在往外渗着血丝的牙印,浅浅的,小小的,就像小姑娘那懵懂的单纯。
我不知道那串冰糖葫芦是否会感到疼痛,我只知道那个傻姑娘往外渗着血丝的手让我感到了心痛。
还记得那日树下,她一袭水青长裙,静立于树前,巧笑倩然,红棉花都失了颜色。
微风抚过她的眉梢,却吹不开她紧锁的眉头,也吹不散那愁绪。
她总是为一些她认为应该伤感的事物而伤感着,我也曾劝慰过她,美好背后的寂寥,与万象更新的代价,我已经在很小心的措辞了,却还是敌不过美人一枝梨花带雨的泪。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她的心中,这世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我们却都是带着罪恶在这世间活着。
春天消融的残雪,夏日干涸的河塘,秋天凋零的落叶,冬日冻死归鸟……如此这些,都成为了一把悬挂在她眉头上的铁锁,锁住了朱颜。
我很少见她笑过,黛眉轻蹙,似是她的常态。
我常笑话她是一个矫情的人,但正是因为这种矫情,才将她与那些庸脂俗粉分隔开来,在我的心中, 她是不同,也是唯一。
我想,我是喜欢上她了。
想起了那串她吃剩下的冰糖葫芦,银牙轻咬,我看得见她眼中闪过的欣喜,却是坚持不肯再吃一口,咽着口水,倔强的将头偏向一边。这样子的她,真的很可爱。
“这是什么?”她问我说。
“你没吃过吗?这叫做冰糖葫芦,一种很美味的小吃。”
“没有~”她咬下一颗,很诚实的点了点头。
她笑的很甜,就像是包裹在山楂上的糖衣,却是转瞬即逝。
“你怎么不吃了?”看着她忽然冷下来的笑颜,没由来的,我忽然赶到有些不安。
“你说,我这样咬它一口, 它真的不会感到疼吗?”话音未落,拴着珍珠的弦就已经断了。
低下头,我正好看到她手背上那个还在往外渗着血丝的牙印,浅浅的,小小的,就像小姑娘那懵懂的单纯。
我不知道那串冰糖葫芦是否会感到疼痛,我只知道那个傻姑娘往外渗着血丝的手让我感到了心痛。
还记得那日树下,她一袭水青长裙,静立于树前,巧笑倩然,红棉花都失了颜色。
 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区别和症状
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区别和症状






![[同人]大风和他皮套的小日常之当大风睡过头](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313/151327_38622.jpg)
![[同人]大风和他皮套的小日常之当大风睡过头](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515/161607_87205.jpg)
![[同人]大风和他皮套的小日常之当大风睡过头](https://wimgs.ssjz8.com/thumbnail/2023/0725/122058_0253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