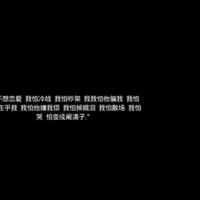小说最后的歌读后感合计(16)
2022-08-14 来源:百合文库
高觉新这个形象时潜在的创作动因。在《家》的自序中,巴金也明确的写明了这一点,他说他写《家》是为了写给他的大哥,因为他觉得他的大哥实在是太辛苦了,为了这个家牺牲了自己。但是他慢慢发现,其实大哥高觉新的形象也是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自己的性格,他们之间是共通的。所以无论从现实中看巴金他们一家她跟他大哥,还是从小说《家》剖析,我们都没有办法将觉新与觉慧的性格完全分离来研究,因为他们都在影响着对方,他们性格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高觉新的性格悲剧性在与,由于历史的安排,也由于自身弱点,他站在了封建家长势力和“家”的青年叛逆者“中间”。正是在这儿,“历史”的形象也呈现了。这两个人物,在“新”与“旧”之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找不到依着旧秩序固有的位置,也找不到依着新思想该有的位置。生存在“过渡时代”爱之一切时代的人们,都可以就某种意义被认为是“站在中间的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但其中的多数,或进或退,趋向分明。惟有高觉新、祁瑞宣所属的这一群,无力地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进退失据。
“家”“国”这两个经常被并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往往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形象,“家”作为老中国压迫和罪恶的代表。不断被控诉、放
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战争时代又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家”成为对离乱的人心和破碎的国土的有效组织形式,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家”“国”想象又以错杂的方式被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叙事中。
在小说中,觉慧成为一个旧家庭制度的反抗者,其实远在真实的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苦闷,他对家庭压迫的感受,基本来自新书报的阅读。在巴金的笔下,觉慧童年时关于人生和世界想象是来自马房中老轿夫讲述的故事,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飘游”;而随着他进入中学,开始阅读新书,他的世界就改变了面目。这些新书报构建了一个古旧腐朽的旧家庭形象,并相应地用一个遥远模糊的乌托邦完成了“离家”的召唤。在《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也是选择了出走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只不过他们出走的方式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出走背后都有他们大哥的牺牲,所以两部小说中这一点很相似。年轻气盛的一代可选择出走去表达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肩负着家族使命的老大,却永远无法轻易地卸下自己的担子去追寻自己的心中的乌托邦。
高觉新的性格悲剧性在与,由于历史的安排,也由于自身弱点,他站在了封建家长势力和“家”的青年叛逆者“中间”。正是在这儿,“历史”的形象也呈现了。这两个人物,在“新”与“旧”之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既找不到依着旧秩序固有的位置,也找不到依着新思想该有的位置。生存在“过渡时代”爱之一切时代的人们,都可以就某种意义被认为是“站在中间的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但其中的多数,或进或退,趋向分明。惟有高觉新、祁瑞宣所属的这一群,无力地跨在两个时代之间的门槛上,进退失据。
“家”“国”这两个经常被并置的概念,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往往构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迅速碎解,出走的新青年一时成为最耀眼的文学形象,“家”作为老中国压迫和罪恶的代表。不断被控诉、放
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被放逐的“家”的意向在战争时代又受到“魂兮归来”的召唤,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家”成为对离乱的人心和破碎的国土的有效组织形式,就像1939年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到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道防线”;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家”“国”想象又以错杂的方式被组织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以及新政权合法性论证的叙事中。
在小说中,觉慧成为一个旧家庭制度的反抗者,其实远在真实的悲剧发生之前。他的苦闷,他对家庭压迫的感受,基本来自新书报的阅读。在巴金的笔下,觉慧童年时关于人生和世界想象是来自马房中老轿夫讲述的故事,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劫富济贫的剑侠,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到处飘游”;而随着他进入中学,开始阅读新书,他的世界就改变了面目。这些新书报构建了一个古旧腐朽的旧家庭形象,并相应地用一个遥远模糊的乌托邦完成了“离家”的召唤。在《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也是选择了出走这种方式来追求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只不过他们出走的方式不同。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的出走背后都有他们大哥的牺牲,所以两部小说中这一点很相似。年轻气盛的一代可选择出走去表达自己心中想要表达的东西,而肩负着家族使命的老大,却永远无法轻易地卸下自己的担子去追寻自己的心中的乌托邦。
 加入罗德岛后的悠闲生活小说
加入罗德岛后的悠闲生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