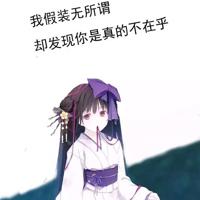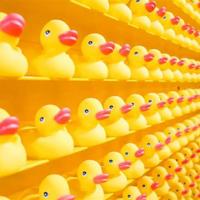汪曾祺鸡毛读后感500精练(6)
2022-08-12 来源:百合文库
故事表述以笔记兼散文的格调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二、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实。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三、小说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二)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与增构。小说《鸡毛》写于1981年6月6日,此时xx已过,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十年劫难后,社会的目光已从高涨的运动场转向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作家以独到的眼光,于平淡中开掘出此学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这种描写与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群体被赋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领社会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进行了消解性的质疑与反思。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普通人的话:“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直觉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们”“真实”的一面时,常常说“可怜”。这种从正面形象的舞台中挖掘的反向、阴暗面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增构。
二、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实。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三、小说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二)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与增构。小说《鸡毛》写于1981年6月6日,此时xx已过,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十年劫难后,社会的目光已从高涨的运动场转向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作家以独到的眼光,于平淡中开掘出此学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这种描写与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群体被赋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领社会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进行了消解性的质疑与反思。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普通人的话:“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直觉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们”“真实”的一面时,常常说“可怜”。这种从正面形象的舞台中挖掘的反向、阴暗面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增构。
 酒巷笙歌鸡毛掸子mf
酒巷笙歌鸡毛掸子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