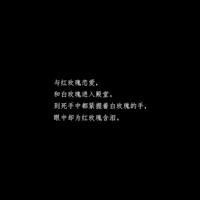周作人《怀废名》读后感汇合(12)
2022-07-08 来源:百合文库
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句子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
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
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
 all炭最后的日柱14
all炭最后的日柱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