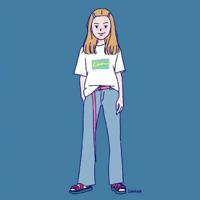《印第安人营地》读后感精练(34)
2022-07-08 来源:百合文库
“不行,我没有带麻药。不过,让她叫去吧。我听不见,反正她叫不叫没关系。”
这时候,那个始终一声不吭的丈夫在上铺转个身靠着墙,他想必是听到了尼克父亲说的话。接着,尼克的父亲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开始了手术:用一把大折刀切开了产妇的肚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有一篇叫《嫌疑》的小说,揭露一个纳粹军医在不注射麻醉剂的情况下就给俘虏作腹部手术,是禽兽所为。而侵华日军也曾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或出于对人类的仇恨,或出于卑鄙的目的。但在《印第安人营地》中,尼克父亲则是在沿着他以为正常的逻辑,在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他不需要拷问自己的良心,因为他“听不见”产妇的惨叫。这和法西斯的兽行比较起来,显得更加荒谬和可怕。
婴儿生出来了,尼克的父亲很得意,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后球员在更衣室里的那种得意劲。他拍拍上铺的产妇的丈夫,揭开蒙着那印第安男人脑袋的毯子:他已经自杀了。这是整个小说的最高潮,可以说压抑的夜色、产妇的尖叫、无麻醉的手术,都是为了抵达这个高潮而作的铺垫,而当高潮到来的时候,海明威不仅一如既往的冷静,而且表现出新闻记者般的精确,其实这正是一切好作家都具有的严峻的克制:
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刀口子拉得好长,鲜血直冒,流成一大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因为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尼克的视角,所以这个男人自杀的动机、过程、他在那个瞬间的念头,都被略去了。海明威借此交给读者的,不仅有疑问,更是那具死了但还冒着鲜血的尸体。每一个细心的读者,都不能不在情感和感官上遭受双重的刺激。他的文字看似无情,所以能让读者伤情,他的冷静近于冷酷,所以他那一刀就像割在我们身上。
我以为,好的小说要有精彩的故事、精致的语言和精妙的结构。还要有立场,立场就是价值观、生死观,这是小说的出发点。还要有心灵,心灵就是同情、悲悯。要让立场消失在叙述中,让心灵从字里行间溢出来。还要有感官,这就是“身体”。身体使小说饱满和丰盈。如果结构是脊梁,语言是质地,身体就是血与肉。血肉之躯才会让故事具有暧昧和神秘。海明威成功的短篇小说,都离不开死亡这个主题,而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身体的消灭,是诉之于感官的刺激,是一刀致命,或者慢慢地腐烂,就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患了坏疽等死的男人。
这时候,那个始终一声不吭的丈夫在上铺转个身靠着墙,他想必是听到了尼克父亲说的话。接着,尼克的父亲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开始了手术:用一把大折刀切开了产妇的肚子。瑞士作家迪伦马特有一篇叫《嫌疑》的小说,揭露一个纳粹军医在不注射麻醉剂的情况下就给俘虏作腹部手术,是禽兽所为。而侵华日军也曾拿活生生的中国人做实验,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开膛破肚。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或出于对人类的仇恨,或出于卑鄙的目的。但在《印第安人营地》中,尼克父亲则是在沿着他以为正常的逻辑,在尽到一个医生的职责,他不需要拷问自己的良心,因为他“听不见”产妇的惨叫。这和法西斯的兽行比较起来,显得更加荒谬和可怕。
婴儿生出来了,尼克的父亲很得意,就像一场足球比赛后球员在更衣室里的那种得意劲。他拍拍上铺的产妇的丈夫,揭开蒙着那印第安男人脑袋的毯子:他已经自杀了。这是整个小说的最高潮,可以说压抑的夜色、产妇的尖叫、无麻醉的手术,都是为了抵达这个高潮而作的铺垫,而当高潮到来的时候,海明威不仅一如既往的冷静,而且表现出新闻记者般的精确,其实这正是一切好作家都具有的严峻的克制:
只见那印第安人脸朝墙躺着。他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刀口子拉得好长,鲜血直冒,流成一大滩,他的尸体使床铺往下陷。他的头枕在左臂上。一把剃刀打开着,锋口朝上,掉在毯子上。
因为这篇小说采用的是尼克的视角,所以这个男人自杀的动机、过程、他在那个瞬间的念头,都被略去了。海明威借此交给读者的,不仅有疑问,更是那具死了但还冒着鲜血的尸体。每一个细心的读者,都不能不在情感和感官上遭受双重的刺激。他的文字看似无情,所以能让读者伤情,他的冷静近于冷酷,所以他那一刀就像割在我们身上。
我以为,好的小说要有精彩的故事、精致的语言和精妙的结构。还要有立场,立场就是价值观、生死观,这是小说的出发点。还要有心灵,心灵就是同情、悲悯。要让立场消失在叙述中,让心灵从字里行间溢出来。还要有感官,这就是“身体”。身体使小说饱满和丰盈。如果结构是脊梁,语言是质地,身体就是血与肉。血肉之躯才会让故事具有暧昧和神秘。海明威成功的短篇小说,都离不开死亡这个主题,而死亡从来不是抽象的,它是身体的消灭,是诉之于感官的刺激,是一刀致命,或者慢慢地腐烂,就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患了坏疽等死的男人。
 第五人格黄衣之主的地下室
第五人格黄衣之主的地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