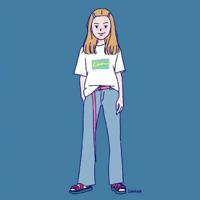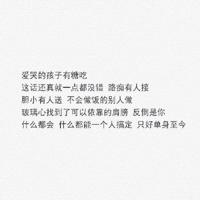认个错繁华过后观后感汇总(98)
2022-05-25 来源:百合文库
张爱玲在作品中不动声色地消灭了这些男性的暴力与霸权,颠覆了男权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扬了女性的力量。
在男权中心意识的受述者(读者)看来,七巧依然摆脱不了“恶妇”、“**”的指责,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对张爱玲作出最有分量评论的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将七巧定位于“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然而,对男性中心意识有着清醒的反省与认识的男性受述者却依然听出了女性立场鲜明的叙述声音,并对傅雷的男权倾向做出了批评指正:“傅雷对七巧的评价充满性别与阶级歧视的话语霸暴力,他称七巧为‘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
将七巧的行为视为‘轻狂’,暴露了傅雷所执的道德标尺——不允许女性表达对情欲,尤其是对‘性’的要求。”傅雷的男权中心意识在文本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叙述声音的干扰下,亦对七巧流露出有限度的同情,“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而对于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女性受述者,却从七巧的“疯狂”里感知到七巧做为一个健康自然的女人对生存、对情欲要求满足的天然合理性,读出了几千年宗法父权的罪恶与腐朽。
张爱玲对《金锁记》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主人公曹七巧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这正影射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实态。曹七巧有女权主义反抗压迫的强烈意识,但她这种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从而导致她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曹七巧是一个戴着金钱枷锁的女人,是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在中国宗法体制中,在女性丧失主体中,在父权政治利益基础上,在宗法体制的关系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的情况下,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大主轴中,无论七巧是循规蹈矩,甘于忍受自己被分配的角色,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都注定要陷入金钱与身体、身体与法、性与爱情两相对立的艰难处境。
在男权中心意识的受述者(读者)看来,七巧依然摆脱不了“恶妇”、“**”的指责,如四十年代上海文坛对张爱玲作出最有分量评论的傅雷先生,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将七巧定位于“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从表面看,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末不足道的渣滓。但命运偏偏要教渣滓当续命汤,不但要做儿女的母亲,还要做她媳妇的婆婆,把旁人的命运交在她手里”,“门户的错配已经种下了悲剧的第一个原因”,“然而最基本的悲剧因素还不在此。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心中偏偏来得嚣张”。然而,对男性中心意识有着清醒的反省与认识的男性受述者却依然听出了女性立场鲜明的叙述声音,并对傅雷的男权倾向做出了批评指正:“傅雷对七巧的评价充满性别与阶级歧视的话语霸暴力,他称七巧为‘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

将七巧的行为视为‘轻狂’,暴露了傅雷所执的道德标尺——不允许女性表达对情欲,尤其是对‘性’的要求。”傅雷的男权中心意识在文本充满理解与同情的叙述声音的干扰下,亦对七巧流露出有限度的同情,“就在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身上,爱情也不会减少圣洁”,“她战败了,她是弱者。但因为是弱者,她就没有被同情的资格了么?弱者做了情欲的俘虏,代情欲做了刽子手,我们便有理由恨她么!作者不这么想。”而对于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女性受述者,却从七巧的“疯狂”里感知到七巧做为一个健康自然的女人对生存、对情欲要求满足的天然合理性,读出了几千年宗法父权的罪恶与腐朽。
张爱玲对《金锁记》描绘的那个年代已离我们远去,可主人公曹七巧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索,这正影射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下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生存的实态。曹七巧有女权主义反抗压迫的强烈意识,但她这种反抗的方式是畸形的,从而导致她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曹七巧是一个戴着金钱枷锁的女人,是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在中国宗法体制中,在女性丧失主体中,在父权政治利益基础上,在宗法体制的关系男女、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身份的情况下,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大主轴中,无论七巧是循规蹈矩,甘于忍受自己被分配的角色,还是离经叛道,反抗命运,都注定要陷入金钱与身体、身体与法、性与爱情两相对立的艰难处境。
 告白认错enigma后顶a怀孕了
告白认错enigma后顶a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