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老虎新娘(10)
我恨不得自己跟父亲农庄上每一个小伙子都在稻草堆里打过滚,就能丧失资格,不必接受这种羞辱的交易。他要的这么少,正是我不能给的原因。我不需要开口说,因为野兽明白我的意思。
他另一侧眼角冒出一滴泪。然后他动了,把嘉年华会的纸板假人头和系着缎带的沉重假发埋进,我想是,他的手臂;他把他的,我猜是,双手从袖子里缩回,我看见他长着毛的肉掌,尖利的爪子。
泪滴落在他毛皮上,闪闪发亮。回到房间,我听见那爪掌在我门外来回踱步,一连好几个小时。
小厮再度端着银盘回来时,我有了全世界最清透水滴般的一副钻石耳环。我将这一枚也扔到原先那枚弃置的角落。小厮难过又遗憾地喋喋自语,但没有表示要再带我去见野兽,而是露出讨好的微笑,透露道:“我主人,他说,邀请小姐去骑马。”
“干什么?”
他敏捷地模仿骑马奔驰的动作,并且,令我大为讶异地发出没有高低起伏的聒噪声:“喀哒哒!喀哒哒!我们要去打猎啰!”
“我会逃走,我会骑马逃冋城里。”
“哦,不。”他说。“难道你不是一位信守诺言的贞洁女士吗?”
他拍了拍手,我的使女滴答答、叮当当地假活过来,朝她原先出来的橱柜滑去,将人工合成手臂伸进橱中,取出我的骑装。竟然是这套衣服,一点没错,正是我留在我们乡间大宅顶楼一口箱子里的那套骑装。那栋位于圣彼得堡城外的大宅我们早就失去了,甚至早在我们出发前来残忍的南方,进行这趟疯狂的朝圣之旅之前。若这不是昔日保姆为我缝的那套骑装,那它就是完美之至的复制品,连缺了一颗纽扣的右袖口、一道用别针别起的裂缝都一模一样。风在宫殿里奔跑,震得门格格颤动,是北风将我的衣服吹过整个欧洲带来这里吗?家乡那个熊的儿子可以随意操纵风的方向,这座宫殿跟那片枞树林有什么共通平等的魔法?或者,我是否该接受这证明了父亲一直灌输给我的那句格言,只要有钱什么都可能办到?
“喀哒哒。”小厮建议道。此刻他眨着眼,显然很高兴看到我惊异愉快交加的表情。发条使女伸手将我的外套递来,我让她帮我穿上,仿佛有些犹豫,但其实我想离开这座死气沉沉的宫殿走出户外想得快疯了,尽管有那样的同伴同行。
大厅的门敞向明亮白昼,我看出时间是早上。我们的马匹已经上了鞍鞯,成为受束缚的野兽,正在等我们,不耐烦的蹄子在地砖上踏出火花,其他马则轻松漫步在稻草间,以无言的马语彼此交谈。一两只蓬着羽毛抵御寒冬的鸽子也走来走去,啄食一束束玉米穗。将我带来此处的那匹黑色小阉马发出响亮嘶鸣迎接我,屋顶下雾蒙蒙的大厅就像回音箱随着马撕振动,我知道这匹马是要给我骑的。
我向来非常爱马,他们是最高贵的动物,明智的眼中充满受伤敏感的神色,髙度紧绷的臀腿充满受理智克制的精力。我对这匹黑亮的伙伴发出唤马的声响,他回应我的招呼,用柔软的唇在我前额一吻。一旁有只毛发蓬乱的小型马,鼻子蹭着壁画马匹蹄下的错视画法枝叶,小厮飞身一跃坐上他背上的鞍,动作灵活花俏有如马戏表演。然后裹着毛皮滚边黑斗篷的野兽来了,骑上一匹神色凝重的灰色牝马。他不是天生的骑马好手,紧攀着牝马的鬃毛像遭遇船难的水手抱住帆柱。
他另一侧眼角冒出一滴泪。然后他动了,把嘉年华会的纸板假人头和系着缎带的沉重假发埋进,我想是,他的手臂;他把他的,我猜是,双手从袖子里缩回,我看见他长着毛的肉掌,尖利的爪子。
泪滴落在他毛皮上,闪闪发亮。回到房间,我听见那爪掌在我门外来回踱步,一连好几个小时。
小厮再度端着银盘回来时,我有了全世界最清透水滴般的一副钻石耳环。我将这一枚也扔到原先那枚弃置的角落。小厮难过又遗憾地喋喋自语,但没有表示要再带我去见野兽,而是露出讨好的微笑,透露道:“我主人,他说,邀请小姐去骑马。”
“干什么?”
他敏捷地模仿骑马奔驰的动作,并且,令我大为讶异地发出没有高低起伏的聒噪声:“喀哒哒!喀哒哒!我们要去打猎啰!”
“我会逃走,我会骑马逃冋城里。”
“哦,不。”他说。“难道你不是一位信守诺言的贞洁女士吗?”
他拍了拍手,我的使女滴答答、叮当当地假活过来,朝她原先出来的橱柜滑去,将人工合成手臂伸进橱中,取出我的骑装。竟然是这套衣服,一点没错,正是我留在我们乡间大宅顶楼一口箱子里的那套骑装。那栋位于圣彼得堡城外的大宅我们早就失去了,甚至早在我们出发前来残忍的南方,进行这趟疯狂的朝圣之旅之前。若这不是昔日保姆为我缝的那套骑装,那它就是完美之至的复制品,连缺了一颗纽扣的右袖口、一道用别针别起的裂缝都一模一样。风在宫殿里奔跑,震得门格格颤动,是北风将我的衣服吹过整个欧洲带来这里吗?家乡那个熊的儿子可以随意操纵风的方向,这座宫殿跟那片枞树林有什么共通平等的魔法?或者,我是否该接受这证明了父亲一直灌输给我的那句格言,只要有钱什么都可能办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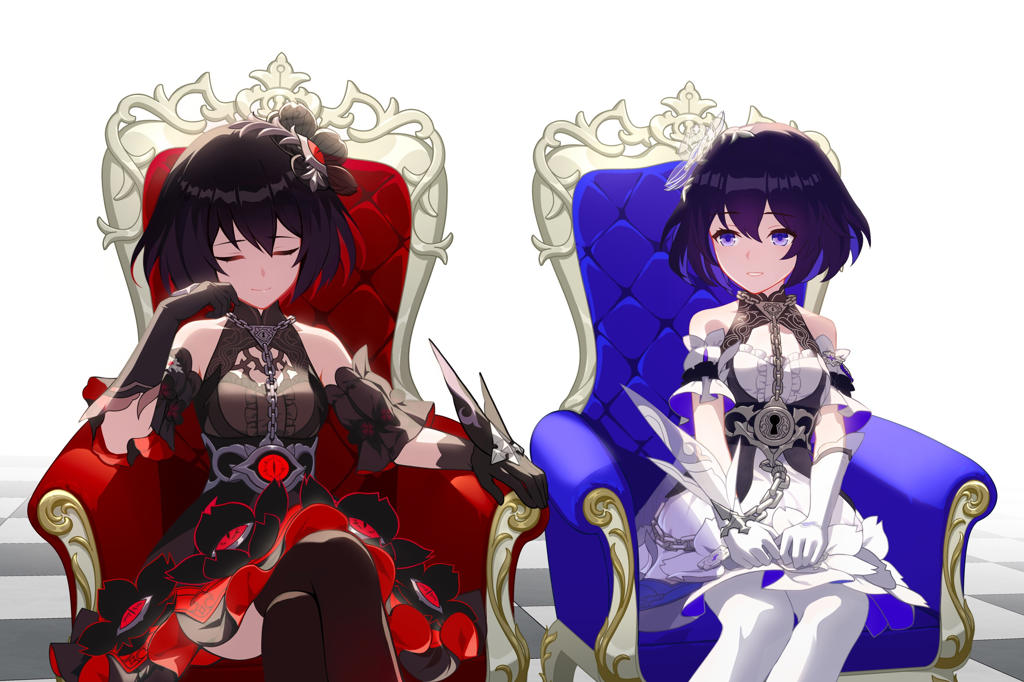
“喀哒哒。”小厮建议道。此刻他眨着眼,显然很高兴看到我惊异愉快交加的表情。发条使女伸手将我的外套递来,我让她帮我穿上,仿佛有些犹豫,但其实我想离开这座死气沉沉的宫殿走出户外想得快疯了,尽管有那样的同伴同行。
大厅的门敞向明亮白昼,我看出时间是早上。我们的马匹已经上了鞍鞯,成为受束缚的野兽,正在等我们,不耐烦的蹄子在地砖上踏出火花,其他马则轻松漫步在稻草间,以无言的马语彼此交谈。一两只蓬着羽毛抵御寒冬的鸽子也走来走去,啄食一束束玉米穗。将我带来此处的那匹黑色小阉马发出响亮嘶鸣迎接我,屋顶下雾蒙蒙的大厅就像回音箱随着马撕振动,我知道这匹马是要给我骑的。
我向来非常爱马,他们是最高贵的动物,明智的眼中充满受伤敏感的神色,髙度紧绷的臀腿充满受理智克制的精力。我对这匹黑亮的伙伴发出唤马的声响,他回应我的招呼,用柔软的唇在我前额一吻。一旁有只毛发蓬乱的小型马,鼻子蹭着壁画马匹蹄下的错视画法枝叶,小厮飞身一跃坐上他背上的鞍,动作灵活花俏有如马戏表演。然后裹着毛皮滚边黑斗篷的野兽来了,骑上一匹神色凝重的灰色牝马。他不是天生的骑马好手,紧攀着牝马的鬃毛像遭遇船难的水手抱住帆柱。
 东方仗助×吉良吉影车
东方仗助×吉良吉影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