雏菊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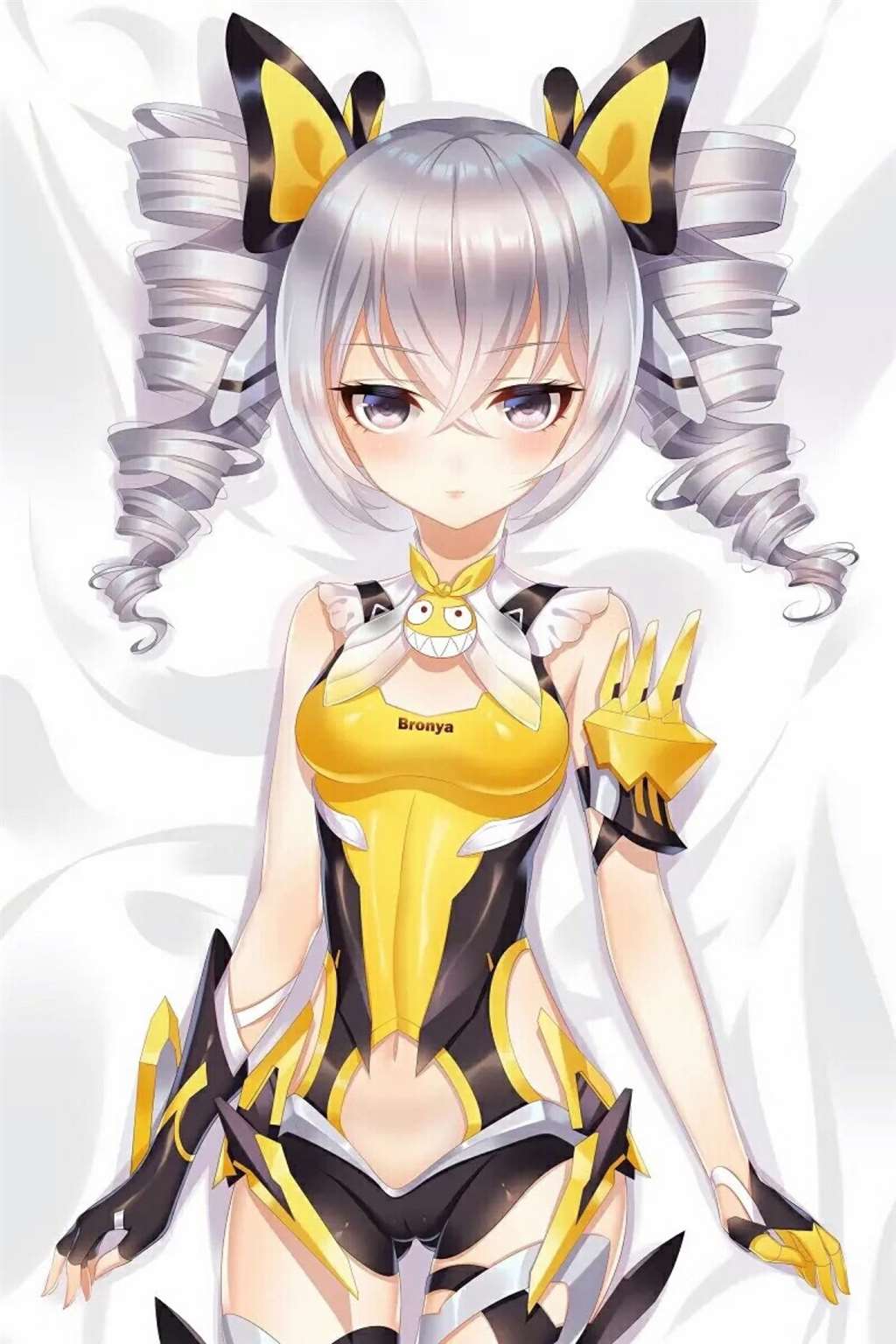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头黑色的柔顺的秀发。果戈里经常趴在他肩上,边抚摸他的头发边说:“最喜欢费佳的头发了,好软啊!”
因为各种原因,或许果戈里的喜爱也是其中之一,他迟迟未剪去过长的头发。低头时过长的碎发遮挡视线,看不世界的原貌,但剪去就能看清了吗?还是果戈里担心扎进眼睛里难受,用个小发夹帮他把多余的头发固定住。发夹上开着一朵精致的金属雏菊,花瓣漆成圣洁的白,花心漆成明亮的鹅黄,像真的一样。只是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什么呢?他思考许久未果。
直至有天黄昏,果戈里不知从哪儿搞来一束开得灿烂的真雏菊插到花盆里。他似乎累极了,用手环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脖子,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背上睡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阅读,头上着可笑的发夹。
太阳已经有一半沉下去,天边紫色、黄色、红色等颜色混杂在一块儿,共同织就绚烂的天空。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雏菊的清香,没栀子花的甜腻,没兰花的寡淡,仅觉得很新鲜、很温馨。
他的左抚上果戈里散落的发,是耀眼的全色。漫不经心地撩起一绺,一圈一圈地绕着。他觉得果戈里的头发才是最软的。右手翻页,闻到花香,他似有所悟,是少了香气吧,确实是吧。
同时听见果戈里均匀的呼吸,他又茫然起来。
少了什么呢?是生命和未说出口的爱。
 《菊内留香》TXL金银花笔趣阁
《菊内留香》TXL金银花笔趣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