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自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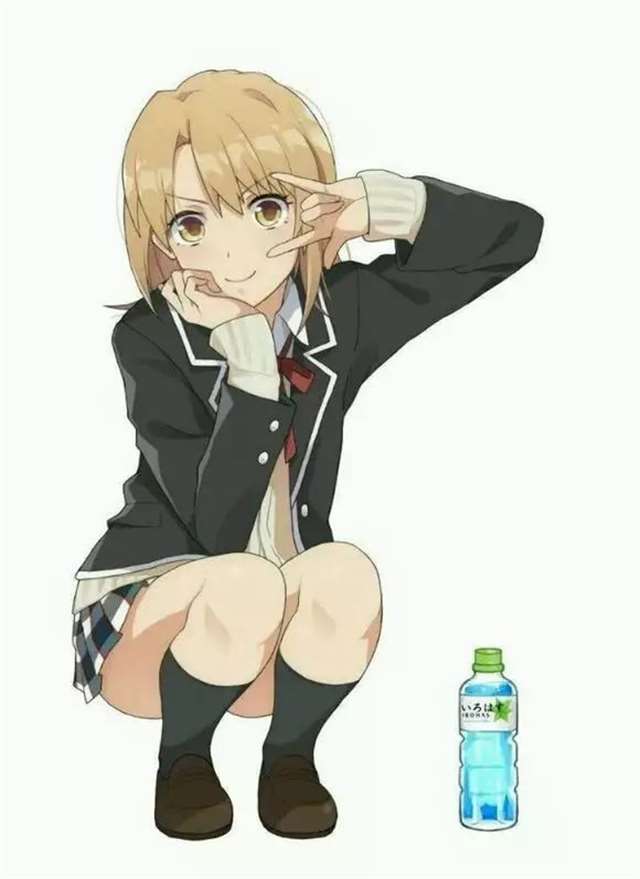
六月的最后一天
鼠君是上午死的,晚上埋的。这其中本身没有什么含义的,却固然因为死而带上了神秘色彩。总之中午我去时,鼠君是没有死的,只是晚些时候,大约是两点一刻时,从我朋友梁君那里传来了他的死讯,他说,“鼠君死了,我们将它葬了,可好?”我冷冷地瞪了他一眼,不可置否的回答,“鼠君死了?那就死了!”
梁君没有什么表示,只是淡淡的摇了摇头,便坐下了。下午的课本来就是难熬的,再加上雨后,空气就更加的灰暗,了无生趣,又回想到了鼠君的事,外面的乌云便又聚了起来,看起来又要下雨了。
灰暗的教室,一个站着的人头,和一群埋着的人头,独我是高昂着脑袋,想着鼠君的死,不是其他的人头,残忍,冷酷,估摸着是鼠君死的,死的太过微小,太过微小了,所以更谈不上其他的感伤与杂思,这个世界的生命那么多,我岂会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鼠君而感到伤心?谈不上吧!但那种窒息,还在掐着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站起来,周围的人头和站着的人头看向我,带着审视,还有惊诧,我不动,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站起来,连忙解释到,“有点闷,可以开一下窗子吗”
它们又因为我这无关紧要的话继续运行,真正此时不知怎地,我突然向它们喊起来,“鼠君的死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吗?”周围的人头都纷纷涌动,鼠君是谁?对啊,他们连鼠君都不知道是谁?更何况是他的死,那个站着的人头恶狠狠的看着我,生气的他伸手将我丢出了窗外,我会死吗?我也要像鼠君那样,毫无紧要的死去吗?外面的雨下的很大。这是我失去意识前的感受。

 信白李白自己扩张
信白李白自己扩张


















